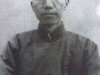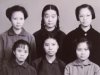(一)官僚群体的分化:并非所有官僚都已经异化
官僚阶层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其内部存在深刻的分化:
1、坚守信念的群体:有相当数量的官员,特别是基层和中层干部,他们可能因为缺乏权力变现的渠道,更可能因为保留了最初的理想信念,从而保持了相对的廉洁和职业操守。他们是体制内保持基本运转和道德底线的力量。
2、不作为与无奈:另一些官员可能出于清廉的自我保护或对体制的失望,选择在工作中保持消极不作为。尽管这种状态并非积极的推动力,但也避免了他们成为腐败的直接推手。
因此,将整个官僚阶层简单地等同于“资产阶级”,是过于粗糙且不准确的概括。
(二)红色权贵的反思:背叛阶层的良知力量
更引人注目的,是少数红色权贵家族的成员。他们虽然出生于特权顶层,拥有无可比拟的资源和优势,但却自觉或不自觉地背叛了其阶层的既得利益,选择了更高的价值追求。
1、对普世价值的顺应: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教育、反思和对历史的理解,深刻认识到权力世袭和特权固化的危害,转而认同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人类普遍的价值准则。
2、体制内的“异见者”与改革推动者:他们可能利用自身的特殊地位,在体制内部发出不同的声音,推动渐进式的改革和进步。他们的发声往往比普通民众更具穿透力和保护性。
3、历史的良心:这些选择站在人民一边、批判和反思自身阶层特权的个体,构成了民族的良心和希望所在。他们的存在证明了人性并非完全由阶级利益所决定,在关键的历史节点,道德勇气和理想信念可以超越血缘和利益的束缚。
在腐蚀和异化占据主导趋势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体制内部也存在着分化与反思的力量。这些未被异化的官僚和反叛特权的红色精英,是体制内稀有的良知资源。他们是推动社会向更公平、更公正、更开放方向发展的潜在希望,也是打破特权固化、防止理想信念彻底沦丧的最后一道防线和火种。
十二、危机与救赎
无产阶级革命的异化与权贵阶层的滋生,是一个深刻的体制性问题,而非简单的个人道德问题。它揭示了:在权力高度集中且缺乏有效制衡的公有制体制下,政治权力会成为比经济资本更具支配性和剥削性的资源。
这个新阶层,既不符合经典理论中“无产阶级”的定义,也不完全符合“资产阶级”的定义。他们是国家权力垄断公有财产这一体制下特有的产物,是高昂体制成本的制造者。当今中国地方财政趋近崩溃,绝非简单的经济周期问题,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官僚特权阶级和特权结构的必然历史代价。
财政失衡是体制成本畸形膨胀的结果,而体制成本的畸形膨胀,正是权力脱离人民监督、为自身利益服务的具象化表现。
(一)特权阶级的滋生是体制成本膨胀的根源
如前所述,无产阶级政权在革命成功后,其核心权力逐渐被红色权贵和官僚阶层所垄断。这种异化是财政危机的深层病灶:
1、权力的私有化:官僚不再是“公仆”,而是掌握行政权、资源分配权和信息权的“主人”。他们利用公权力将公共资源和国家资本转化为私人财富和家族利益,构成了官僚权本阶级。
2、体制的工具化:庞大的行政和事业单位体系,不再单纯服务于社会治理,而成为分配政治和经济利益、安置权力家族成员、巩固特权统治的工具。体制成本不再是治理成本,而日益成为维护特权和内部消化的成本。
(二)特权阶级对社会资源虹吸,是导致体制成本膨胀又一原因
在异化产生的特权结构下,财政体系必然遭受成本刚性膨胀的压力:
1、行政冗余的必然性:官僚权本阶级需要不断扩张其权力边界和控制范围,以确保其利益和就业。这导致行政人员、事业单位人员、各类“编外人员”、“维稳人员”规模空前膨胀,形成了庞大的“供养阶层”。这些人员的工资、福利、养老金成为财政上的超刚性支出。
2、支出的无效性:缺乏有效监督和制衡,财政支出被大量浪费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低效的重复建设。这进一步加剧了财政的空心化,财政投入并未转化为可持续的社会生产力。
3、收入的掠夺性:为了弥补天价的体制成本,地方政府转向掠夺性收入模式——最典型即是土地财政。这种模式以透支未来发展、加剧社会不公为代价,饮鸩止渴,最终随着房地产泡沫破裂而彻底坍塌,将异化的全部成本以债务和烂尾的形式,抛给了整个社会。
财政发不出工资,本质是特权阶级对社会资源虹吸的容量已达极限,债务雪球已无法滚动。
(三)救赎:普世价值是重建体制的唯一基石
中国这艘体制巨轮晃晃悠悠行驶至今天,已经渐渐失去了动力,最终只会在历史的海平面漂移,随时可能撞上冰山。随着土地财政的崩溃,三驾马车的火力渐微,维持体制运行的行政预算将入不敷出。要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危机和体制成本奇高的问题,必须从体制的价值内核入手,对导致异化的结构进行彻底重塑。发行债券或调整税收只能缓解症状,唯有普世价值的引入,才是杜绝权力异化的根源。
普世价值,如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权,是制衡权力、保障社会公平的根本工具,它能从根本上铲除官僚权本阶级滋生的土壤:
1、民主:实现权力向人民的回归
真正的民主保障了人民对权力的有效监督权和选择权,杜绝了权力世袭和终身制。当权力对人民负责时,政府就会成为高效的“公仆”,而非奢侈的“主人”,从而压缩无谓的行政冗余和无效开支。
2、法治:约束权力、保障契约
独立的司法和真正的法治能将权力关进笼子。它能有效遏制权力寻租和腐败,斩断官僚与资本勾结的链条,确保市场经济运行在公平、透明的基础上,从而终止对公共财产的掠夺。
3、人权与自由:释放社会活力、创造财富
保障个人的自由、财产权利和创新精神,是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只有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社会活力才能被最大程度地释放,创造出可持续的、强大的社会财富,为政府提供健康的税基,彻底摆脱对土地财政竭泽而渔的依赖。
财政危机表面是经济问题,实质是政治问题;它最终的解决方案,不在于技术上的修修补补,而在于政治体制的价值重塑。只有真正回归并落实普世价值,建立公民社会,将权力重新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异化的温床,最终实现小而高效的政府和可持续的社会发展。y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