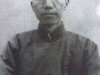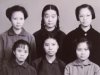(三)示范效应与结构默许
最高层特权集团的财富积累和垄断行为,为体制内其他各级官僚提供了一种“可以被接受”的模式,并在实际操作中,最高层通过权力设置的制度漏洞和监管缺位,客观上纵容了下层官僚的权力寻租。
(四)依附与共生
贫民官僚在追求经济利益时,往往需要依附于红色权贵所掌控的核心资源和项目。这种依附关系使得他们成为权贵集团的外围执行者和利益共享者,共同构成了官僚特权阶级的整体。他们是红色权贵所搭建的特权体系下的受益者和维护者。
因此,红色权贵的异化是无产阶级政权异化的逻辑起点和结构保证。它不仅实现了权力世袭,更通过资本化率先占据了新的统治阶级的核心位置,从而带动并加速了整个官僚队伍的全面腐蚀和特权阶级化。
五、权力异化的历史案例与分析
苏俄、中共建国初期以及前南斯拉夫的历史实践,都从不同侧面印证了权力异化的普遍性,表明了这种现象是权力高度集中体制的内在逻辑。
(一)苏俄(苏联)的“特权阶层”(Nomenklatura)的形成
在十月革命后,苏俄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到了斯大林时代,一套被称为“特权名单制度”(Nomenklatura)的体系最终确立并固化,决定了所有关键职位的任免。这个特权阶层虽然名义上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但在实践中拥有与其级别挂钩的非劳动收入和特权,包括住房特供、商品特供、高级医疗和交通特供等。
在这个案例中,权力异化表现为制度化的分配不公。特权阶层并未通过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进行剥削,而是通过垄断国家权力,将公有财产转化为制度化的特权和个人享受。他们的利益已经与普通工人和农民彻底分离,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新阶层。
(二)中国五十年代末的“反右倾”与政治权力压倒一切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期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决策失误。当党内和体制内的专业人士对浮夸风提出不同意见时,却遭到了政治运动的严厉打击。
这种异化表现为决策权力的失衡。少数最高领导人的意志,通过官僚体系层层传导,成为不容置疑的“真理”。任何基于经济事实和科学理性的反馈都被视为“右倾”或“反党”,专业权力被架空。它展示了:当权力高度集中于少数人,且缺乏制度化的纠错机制时,掌权者为了维护自身路线和权威,宁可牺牲数千万人的生命和国家的经济利益。
(三)前南斯拉夫的“红色经理”阶层
前南斯拉夫实行了相对独特的“工人自治”和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在这个体系中,诞生了一个被称为“红色经理”的群体。他们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人,通过掌握信息、技术和与政府的关系,享有巨大的投资决策权和分配权。
这个群体利用企业的资源为自己创造高额薪酬、优越的福利和投资机会。在20世纪末南斯拉夫解体前的私有化浪潮中,许多“红色经理”利用其在位时的权力,将国有资产低价转卖或转移到自己或关联人的名下,直接完成了从政治权力到私人资本的转化。这个案例清楚地展示了:权力一旦被用来支配经济资源,它就会滋生出一个功能上与资本家无异的特权阶层。
六、文化大革命:一种极端的反异化尝试
从动机和理论层面来看,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除了用于清除他的政治对手外,确实可以被视为一种针对权力异化和官僚特权阶层滋生的极端历史尝试。
(一)理论动机:防止“变修”与继续革命
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核心焦虑,就是担心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后会“变修”(即蜕变为修正主义),担心党内会形成一个脱离人民、压迫人民的官僚精英阶层。他认为:真正的危险不是来自已经被推翻的旧资产阶级,而是来自党内那些掌握权力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他试图通过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夺权和批判,打破旧的官僚体制,重新将权力拉回到无产阶级和普通劳动者手中。
(二)失败的经验:权力、混乱与灾难
然而,历史实践证明,文革最终以一场巨大的失败和灾难告终。它不仅未能解决权力异化的问题,反而带来了更深层次的危机。
1、体制成本的失控:文革彻底破坏了既有的行政秩序、法律系统和生产秩序,导致巨大的社会混乱成本、经济停滞成本和生命代价。这种破坏性的体制成本,远远超过了它试图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