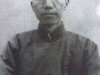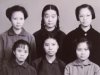2、权力的重新集中:尽管最初的目标是打破旧官僚,但在运动的后期,权力迅速被军事系统和新的革命委员会所掌握。旧的官僚被摧毁后,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更缺乏制衡的军事-政治精英联盟,权力非但没有回到人民手中,反而变得更加专断和集中。
3、未触及权力异化的根源:文革失败的关键在于,它只是一种周期性的、破坏性的运动式尝试。它没有建立起一套制度化、常态化、非人治化的权力监督和制衡机制。它仅仅是通过暴力和运动,将一部分老官僚替换成了另一批新官僚。只要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对公有财产的垄断的体制基础不变,新的特权阶层仍会滋生。
文革的失败证明,以极端、非理性和破坏性方式解决异化,不仅注定失败,还会带来更大的权力灾难。
七、反异化成功的关键:制度化制衡
以文革那种破坏性、运动式的方式来“反异化”,不仅注定失败,还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反异化的成功,必须依赖于制度建设和权力制衡,而不是依赖于人治或政治运动。核心在于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确保掌权者始终能被有效监督和制约。
成功的反异化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一)权力横向制衡(分权)
这是防止权力集中的最根本方法。
1、独立的司法系统:确保法院系统独立于行政和执政党之外,能够根据法律原则,而非政治意志,来裁决行政权力滥用和官员腐败。这阻止了掌权者凌驾于法律之上。
2、立法机构的有效制约:确保代议机构拥有真正的立法权、预算审批权和调查权,能够有效审查行政部门的开支和行为,阻止其随意支配国家资源。
(二)权力纵向制衡(监督与问责)
这是确保权力对人民负责的机制。
1、信息公开和透明化:将政府决策、财政预算、官员财产和行政审批流程最大限度地公之于众。透明度是最好的防腐剂,它让潜在的特权行为暴露在公众监督之下,大大增加了寻租的体制成本。
2、自由的公民社会和媒体:允许独立的媒体、公民组织和学术机构对权力进行批评和曝光。他们充当了“权力异化的警报器”,能够及时揭露和阻止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
(三)权力去垄断化(市场与法治)
这是减少权力支配经济资源范围的关键。
1、建立竞争性市场经济:缩小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和资源配置的权力,让价格和供需关系决定资源流向。这使得掌权者能够寻租的范围大大缩小,从而削弱权力转化为财富的通道。
2、稳固的产权保护和契约法治:确保公民和企业的合法财产受到法律保护,即使面对强大的政府干预也不能轻易被剥夺。这直接限制了官员随意支配和侵占社会财富的权力。
八、对权贵阶级与技术官僚的再审视
在现实的权力运作中,技术管理精英很容易将专业权力转化为官僚权力,再通过寻租转化为资本,这两者往往是重叠、融合和转化的。
(一)权贵阶级其实是“官僚特权资产阶级”
“官僚特权资产阶级”这个称谓对于描述那些利用职权直接攫取经济利益的群体,是更准确、更具有批判力的。核心动作是权力与资本的直接联姻。
“官僚”:体现了其权力来源是行政或政治地位。
“资产阶级”:体现了其利益获取方式是通过资本收益和对生产资料(或企业股权)的间接占有,而不是通过合法的劳动所得或仅仅是行政特权。
官员参股或拿干股现象,是权力异化或权力资本化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所有权和收益权上的侵占。此时,他们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官僚”,而是蜕变成了享有官僚特权的资产阶级。
(二)技术官僚的价值与局限
“技术官僚”概念更多强调现代治理的复杂性。即使在一个清廉的政府中,掌握复杂经济和技术知识的精英群体也必然拥有巨大的决策权(知识对民众的垄断)。但在当前的现实中,权力利用市场经济的外壳,为自身进行资本积累是更主要、更急迫的问题。因此,与其说是纯粹的“技术官僚”,不如说现在权力异化的主流表现是:体制内的精英群体,利用其“官僚权力”(行政审批、资源支配),直接或间接参与到资本运作和利润分配中,形成了特权与资本合流的“官僚权本阶级”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