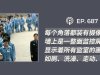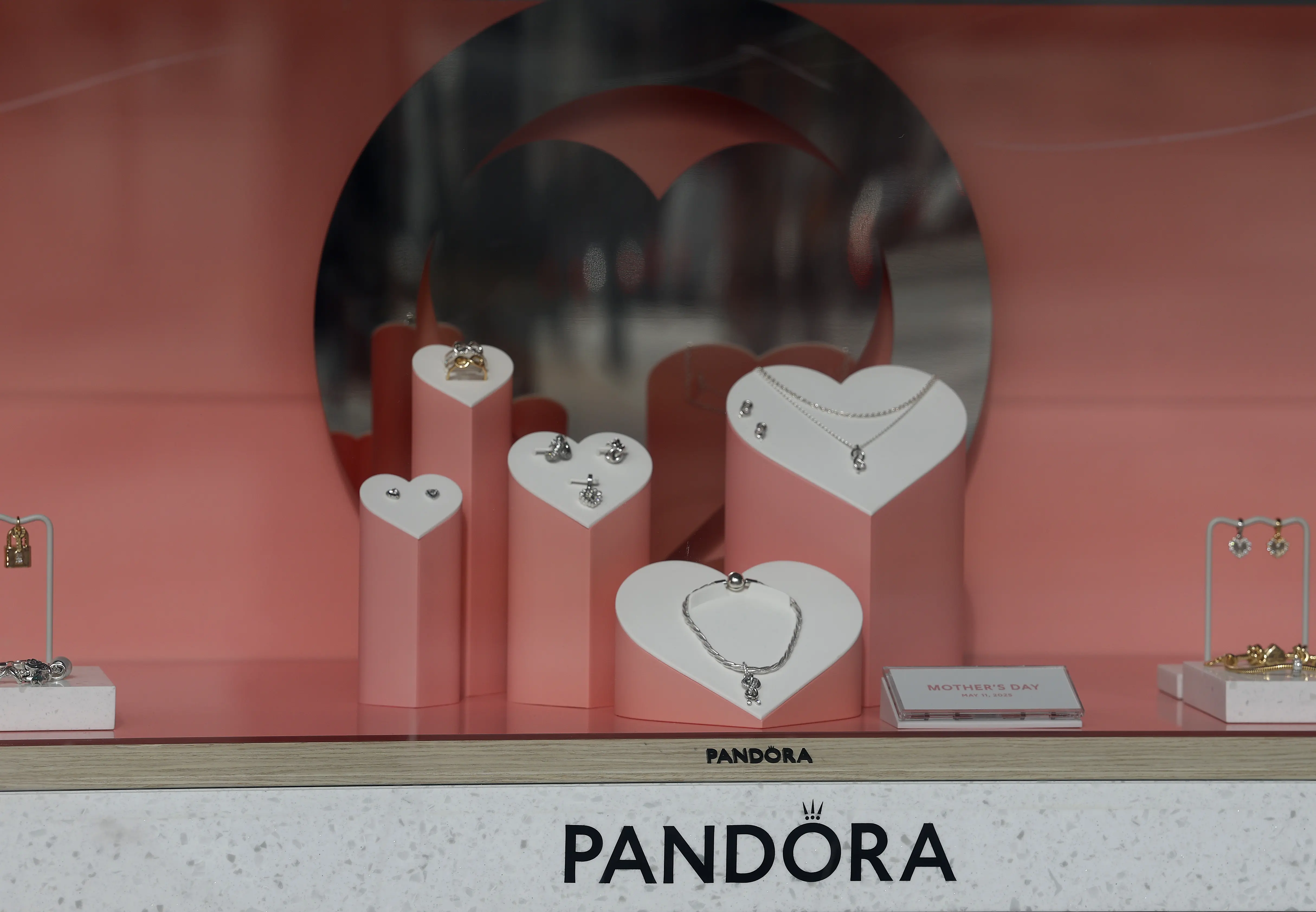
丹麦轻奢首饰品牌潘朵拉(Pandora)公告,将在中国关闭100家门店。图为美国旧金山一家潘朵拉饰品店的橱窗。
2025年8月15日,丹麦轻奢珠宝品牌潘多拉(Pandora A/S)宣布,将中国市场原计划关闭50家门店的规模扩大至100家,现有门店数量将减少约57%。同时启动大规模裁员,销售人员在关店后将获得赔偿,但不会被调往其它门店。这一决定标志着潘多拉在中国市场的重大战略收缩,引发公众广泛关注。
作为曾年销一亿件首饰、位居全球珠宝销量前三的轻奢巨头,潘多拉从“少女梦想的象征”到如今被年轻人集体抛弃,其衰退不仅是一场品牌危机,更是中国消费生态深刻转型的缩影。本文将从潘多拉的兴衰历程、败退原因、全球市场对比及启示等方面,剖析其在中国市场所面临的困境,并探讨这一现象对消费文化与经济的深远影响。
潘多拉的兴衰历程
1982年,Per Anabelsen夫妇在丹麦哥本哈根创立珠宝零售店,并在1984年注册了潘多拉品牌,专注DIY串珠手链。通过建立泰国生产基地和全球销售网络,其形成了原料、物流、销售一体化的闭环模式,这一高效且低成本模式,推动潘多拉从一家地方零售商快速扩展至全球。
2008年,丹麦私募股权集团Excel(Axcel前身)收购60%股份,进一步加速其国际化进程。2010年,潘多拉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市值从80亿丹麦克朗暴增至330亿丹麦克朗。泰国制造基地、丹麦设计中心与全球直营网络,构成高度整合的商业模式,潘多拉成为全球轻奢珠宝的明星品牌。
2015年,潘多拉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彼时正值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产阶层日益壮大。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升,消费观念从“满足基本需求”转向“追求品质与个性”。潘多拉精准填补了高端奢侈品(如LV、卡地亚)与快时尚饰品之间的市场空白,以“国际轻奢”定位迅速走红。
其核心产品:可定制串珠手链,强调“一颗珠子一个故事”,允许消费者自定义组合,赋予人们参与感和情感共鸣。而亲民价格(手链约600元,串珠约200元)和高频新品(每年7次上新,超700款式)则进一步刺激消费热潮,令其迅速占领了中国三四线城市商场。
在“轻奢定制”“独一无二”的故事包装下,潘多拉一度成为中产女性和年轻群体的“必备信物”。潘多拉手链不仅是一件珠宝,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每一颗串饰都承载着旅行、友情、爱情的纪念意义,年轻人愿意为它排队、打卡、分享,引发一种社交性的消费狂热。
2016年,潘多拉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暴涨175%。2019年,更是达到了巅峰的19.7亿丹麦克朗,占到其全球营收的9%,门店扩张至240多家。本质上看,潘多拉在中国的崛起主要依赖于外部红利——消费升级浪潮。其复制了国际模式,却未充分本土化,这为后来的衰退埋下隐患。
潘多拉在中国市场的下滑并非突发,而是从2020年疫情爆发后开始的持续性萎缩。从2021年起,潘多拉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呈现断崖式下跌:2021年11.26亿丹麦克朗,2022年7.37亿丹麦克朗,2023年5.64亿丹麦克朗,2024年仅4.16亿丹麦克朗。
进入2025年,情况更为严峻。一季度,销售额仅9,600万丹麦克朗(约1.1亿元人民币),同比下滑11%;二季度可比销售额下跌15%,而同期全球销售额则增长3%。连续几年下跌后,中国市场营收占比从9%降至1%,门店数量从240多家缩减至180多家。
退败原因的深入分析
潘多拉在中国市场的败退源于多重因素的叠加,这些因素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主要体现在消费偏好、产品缺陷、市场竞争和成本压力四个方面:
第一、消费偏好结构性转变。近几年,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消费的核心逻辑已从“感性驱动”变为“理性判断”,购买决策时强调保值性和实用性。年轻群体从“装饰性消费”转向“资产性消费”,黄金因兼具文化认同、避险属性和保值功能,成为其投资和日常佩戴的首选。
2025年上半年,中国黄金市场成交量和成交额大幅增长,其中,金条及金币消费量同比增长23.69%。相比之下,潘多拉以“装饰属性”为主的银饰品溢价高却不保值,彻底失宠。DIY串珠的“情感故事”理念在保值导向下失效,消费者宁愿选择价格相近的金豆,也不愿投资“买了就贬值”的银饰。
第二、产品设计和材质问题进一步加速衰退。首先,潘多拉设计缺乏辨识度。卡地亚有猎豹、宝格丽有灵蛇、香奈儿有双C,而潘多拉数百款饰品无标志性符号,被消费者戏称为“义乌小饰品”,无法承载身份象征,失去了高级感。
其次,材质问题更为严重。潘多拉饰品主材为铜银合金、925银、氧化锆石和珐琅等廉价材料,容易氧化发黑且保养麻烦,需预约清洗维护,繁琐且易损坏,严重影响消费者体验。潘多拉的产品本质上是廉价材料的溢价包装,如不能从根本上提升材质价值,品牌就会从“轻奢”滑向“伪奢”。
最后,在二手市场上,潘多拉饰品几乎无人问津,原价上千元的饰品仅值几十元,甚至被回收商拒收。这种“买了就贬值”的特性与消费者对保值性的追求背道而驰,打击了品牌形象,使潘多拉失去了轻奢品牌最重要的信任感。消费者一旦认识到品牌故事与实际价值不符,信任便难以重建。
第三、市场竞争格局重塑。首先,传统高奢品牌如蒂芙尼、宝格丽凭借深厚底蕴、优质工艺和材质推出年轻化系列,抢占追求品质和品牌价值的高端客群。其次,本土珠宝品牌如周大福、周生生依托市场积累,推出兼具时尚设计与保值功能的金饰产品,受到消费者欢迎。
最后,新兴品牌不断涌现。如HEFANG以快速上新、价格亲民、设计紧跟潮流等特点,吸引了大量追求时尚且注重性价比的年轻消费者。这使得潘多拉的“轻奢定制”定位陷入尴尬:相较高端珠宝,缺乏品牌壁垒和收藏价值;相较黄金,缺少硬通货属性;价格高于快时尚饰品,性价比不足。
此外,潘多拉的营销手段明显滞后。例如,HEFANG通过《玫瑰的故事》等剧集将品牌与“女性独立精神”绑定,精准击中年轻群体。反观潘多拉却仍依赖传统广告,线上销售占比不足20%,与数字化消费潮流脱节,未能有效触达年轻群体。
第四、原材料价格上升增加成本压力,削弱了品牌竞争力。白银是潘多拉珠宝的关键原材料,价格攀升至15年高点,为对冲成本,潘多拉两次提价共9%,但却直接削弱了性价比,打击消费意愿,导致客户流失。
同时,潘多拉坚持高成本直营模式,门店租金、人力成本等固定支出沉重,导致盈利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当中国市场增长停滞后,这一模式成为了企业的包袱,形成恶性循环。
全球市场的对比与启示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市场持续萎缩,但潘多拉全球业绩仍保持增长。2025年二季度,全球营收70.75亿丹麦克朗,同比增长4.5%;净利润8.03亿丹麦克朗,略高于上年。其中,美国市场贡献34%营收,同比增长10%,成为集团主要利润来源。
增长得益于美国市场强劲需求,尤其是母亲节期间的消费拉动。美国消费者仍追求个性化装饰,DIY串珠掀起“改造潮”,甚至被改造为头饰、腰带等,并借助TikTok病毒式传播,受到年轻人广泛追捧。中国消费者对保值性的追求与美国消费者对个性表达的偏好形成鲜明对比。
中美市场的差异揭示了更深层的现实:在成熟消费市场(如欧美),个性表达仍是主流文化;而在经济增速放缓、财富焦虑加剧的中国,消费者则更加注重保值、安全与实用。换言之,潘多拉不是“失去了全球吸引力”,而是失去了中国式的中产信仰。
潘多拉在中国市场的退败,是中国轻奢时代退潮的一个象征。“轻奢”基于中产阶层崛起与财富预期的稳定,它满足“既想拥有奢侈外观,又不愿承担奢侈成本”的心理平衡。然而,当房地产红利消退、债务压力加重、就业竞争加剧,中产阶层的安全感被削弱,消费结构便不可避免地收缩。
当下的消费者更加务实:他们会计算“每一笔消费的长期价值”,而非被情绪驱动。珠宝不再是浪漫的象征,而成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黄金、投资首饰、二手奢侈品的流行,正是这种心理转变的反映。而那些依靠“故事营销”维系溢价的品牌,正在迅速失去立足之地。
面对困境,潘多拉进行了多种自救措施:进驻北京王府中环、太古里等高端商圈;邀请许光汉、宋祖儿等年轻明星代言;与迪士尼、漫威、王者荣耀IP联名;甚至跨界开设“潘多拉咖啡店”。另外,潘多拉还尝试从直营转向授权本地零售商运营,以降低固定成本。
然而,这些尝试均未能扭转颓势,高端商圈客流有限,明星代言难以拉动复购,联名产品效应昙花一现,跨界咖啡最终亏损关店。任何营销创新都难以掩盖其产品与市场逻辑的错位,品牌授权模式的转型,或能减轻财务压力,但无法改变品牌吸引力下降的事实。
关闭100家门店后,潘多拉在中国大陆门店将不足百家。潘多拉的败退并非孤例,过去几年,多个外资品牌在中国出现类似趋势。从MUJI到ZARA,从家乐福到潘多拉,无一例外地遭遇了同样的困境——中产消费的收缩与结构性调整。
这反映出中国经济的深层变化:财富分配结构趋向两极化,中间层收入增长停滞;房地产财富效应消失,家庭资产预期下降;消费者信心不足,储蓄倾向上升;年轻群体“低欲望化”,消费更注重必要性与性价比。在这种背景下,介于奢侈与大众之间的轻奢品牌,最先被边缘化。
结语
潘多拉在中国市场的败退源于消费者偏好转变、产品缺陷、竞争加剧及战略失误等多重叠加效应。其早期成功得益于消费升级红利,但随着“反向消费”成为新趋势,黄金取代银饰成为“保值之选”,这意味着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从“炫耀消费”到“生存消费”的深刻转型。
潘多拉在中国的关店潮不只是一个品牌的困局,更是中产幻象破灭与消费结构再平衡的现实反映。房地产泡沫破灭、债务高企、人口老化导致中产“轻奢梦”破碎,社会心理就此发生转折,当保值比浪漫更重要,当“悦己消费”让位于“谨慎支出”,一个时代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