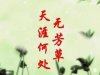步入词坛的苏轼,仅用了四五年时间就写出千古流传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那是1076年的中秋节,40岁的苏轼面对一轮明月,怀念自己的弟弟苏辙,趁酒兴正酣,挥笔而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水调歌头》
当时,苏轼已调离杭州,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有两年了。写完这阕词的第二年,他又被调到徐州,然后调到湖州,直到一场差点要了脑袋的牢狱之灾降临他的身上。

▲我欲乘风归去。图源:纪录片《苏东坡》截屏

1079年,元丰二年。命中大劫,苏轼差点扛不过去。
有人拿他的诗和给朝廷的上表,搞文字狱,说他讥讽朝政。朝廷下令,抓人!
当时苏轼在湖州任知州。从帝都开封到湖州颇费时间,新党骨干、御史台中书丞李定,为寻找执行逮捕任务的人选而发愁,考虑许久,选中皇甫僎作为抓人领队。
皇甫僎带着他的儿子与两名台卒,日夜兼程,奔赴湖州。这时,驸马都尉王诜给苏轼的弟弟苏辙通风报信。苏辙立即派人赶往湖州,希望赶超皇甫僎,好让哥哥提早得知消息,做好心理准备。
皇甫僎的儿子不巧途中生病,耽搁了行程。这样,苏轼提前知道了即将到来的命运。
然而,当皇甫僎一行人出现在湖州地方官署时,苏轼还是相当惊恐。根据他事后的回忆,两名抓人的士兵拘捕他一个地方官,就跟抓一个盗贼一样。
苏轼预料自己必死无疑,首先想到的是跟妻子告别,给弟弟苏辙留封遗书,托付后事。船行到太湖,他欲投水自尽,但想到一死可能连累弟弟,他忍住了。
苏轼下狱的日子里,一些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另一些人则替这名当世第一大才子求情。连他的政治对手、已经退隐金陵的王安石,也替他求情:“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某天入夜,一个陌生人进入苏轼的牢房,未发一言,便在他的身边躺下睡觉。第二天醒来后,那人对苏轼说了一句“恭喜啊”。苏轼一脸迷惑,不知何意。人家笑了一下,说:“安心熟睡就好。”说完就起身,离开了牢房。
后来,苏轼才知道,那是皇帝派来监视他是否有不臣之心的人。人家发现苏轼睡得香,就知道他心中没有鬼,于是回去复命了。宋神宗本来不舍得杀苏轼,这下终于可以对大臣们说:“朕早就知道苏轼于心无愧。”
在狱中待了四个多月后,朝廷的判决下来了,苏轼被贬官黄州(今湖北黄冈)。
出狱当天,苏轼又写起了诗: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末句用了一个典故,说的是唐代长安城里以斗鸡闻名的贾昌,年纪轻轻就受到了喜爱斗鸡游戏的唐玄宗的宠信。苏轼的言外之意,是说如今朝廷上都是投皇帝所好的谄媚之人,我可不与这些人为伍。
写完,他知道自己又犯忌讳了,无奈掷笔大笑:“我真是不可救药。”
谪居黄州,苏轼名义上是团练副使,一个并无实权的小官,实际上属于朝廷的监管人员,并不能随意离开。黄州因为苏轼的到来,而成为文学史上的精神坐标。在那里,宋词史上豪放派的经典之作《念奴娇·赤壁怀古》,正在等待他来书写。在那里,他度过了一生最痛苦的时期,也完成了自己的精神炼狱。
在那之前,他的人生基本上顺风顺水,是被当作“太平宰相”来预期的。但如果没有这些挫折和磨砺,也就不会有如今世人熟悉的超脱豁达的苏轼。
初到黄州的苏轼还无法接受人生的骤然坠落。他几乎断绝了与友人的来往,慢慢调适自己的状态。寓居黄州定慧院,他写过一阕词,词中透露了他孤寂而又独立的心态: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安定下来后,苏轼说自己“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客至,多辞以不在,往来书疏如山,不复答也。此味甚佳,生来未曾有此适”。任性,疏散,当被抛离了帝国官场升迁的正常轨道之后,苏轼终于发现了人生的新天地。
他成为一个农民。跑到田间、集市、江畔,跟各种人聊天。如果人家说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他就请求人家给他讲个鬼故事。人家推辞说没有鬼故事。他却说,瞎编一个也行。他很享受这种没人知道他的身份和经历的状态,“自喜渐不为人知”。
也正是从黄州之后,苏轼成为了历史上潇洒的苏东坡——尽管“东坡”这个号,实际上起源于窘迫的现实。
在黄州,苏轼一家的日常开支十分节俭,但由于没有收入,他带到黄州的钱顶多也只够撑一年。一年后,苏轼一家陷入了窘境。这时,追随苏轼到黄州的好友马梦得发现了黄州城东一片荒芜的坡地,遂向官府申领了那块地。
马梦得跟苏轼同年同月生,同为摩羯座。用苏轼的话说,这个星座“无富贵人”,所以他和马梦得都是穷鬼,但如果一定要分出谁是穷鬼的冠军,则马梦得一定当仁不让。这个比苏轼还倒霉的穷鬼,却帮苏轼要到了一块可以维持生计的荒地。
苏轼将这片无名高地称为“东坡”,从此自称为“东坡居士”。
他沉浸在做农民的日子里。选好了一个日子,他在东坡上放了一把火,烧掉了上面的杂草。如有神助,大火过后,他发现了一口暗井——从此在这里耕种,灌溉不成问题。他买了一头牛,添置了锄头、镰刀等农具,在地里种麦子。收成后,他让妻子王闰之用小麦和小米掺杂在一起做饭。孩子们觉得难以下咽,他却吃得很香。
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王弗病逝后,她成为苏轼的继室。她知道苏轼好酒,却又酒量差,但从不阻止苏轼喝酒。如果苏轼心情烦闷,她就会说,我给你弄一些酒吧。
苏轼似乎很满足于耕种的日子,清晨带着农具和一只酒壶出门,累了就喝口酒,困了就倒在土地上睡去。在给友人的信里,他介绍了自己的“产业”:五间屋子,十余畦果树和蔬菜,一百余颗桑树。
夜里,他会在灯下一遍遍抄写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在词里,他认为自己的前生就是陶渊明:“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
有一次,他和朋友们在深夜里喝酒,醉了又醒,醒了又醉,回家已是三更时分。他站在门外,敲门无人应答,只听到家童熟睡的鼾声。他只好蜷着身子,坐在门前,依稀听到暗夜里传来江水拍岸的声音: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轼《临江仙》
这阕词在黄州城传开后,人们说,苏东坡唱罢此歌,把衣冠挂在江边,乘舟远去了。黄州知州徐君猷听到这个消息,紧张得要命——他对苏轼负有监管责任,于是赶紧跑到苏轼家。到门口,却听到了苏轼的鼾声。这才放下心来。
对于苏轼而言,他要考虑的是如何在黄州安居下来。东坡毕竟是一块官地,难保哪天就被收回去,所以苏轼想自己买一块地。
春天,他跟着朋友到黄州东南的沙湖去看地,走到半路,突然下起了大雨。同行的朋友都觉得很狼狈,只有他淋雨淋出了一阕好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定风波》
当他和友人再次游览黄州城外的赤壁矶,他早已不再执着于个人的境遇。历史的交叠与风景的陶冶,铸造了一颗旷达之心。他写下了被誉为“古今绝唱”的经典词作: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一个涅槃后的苏轼,归来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击垮他。

▲四川眉山三苏祠。图源:图虫创意授权

在苏轼被贬黄州的四年时间里,皇帝未曾把他遗忘。
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被移贬汝州。汝州离北宋的政治中心不太远,这意味着苏轼政治境遇的改善。苏轼原本想上谢表,说明自己愿意终老于黄州,但想想这毕竟是宋神宗的一番好意,只好作罢。
他要离开自己用心经营的田宅,以及好不容易安顿下来的环境和内心,还是颇有些不舍。在不久之前,他刚跟友人要了一批柑橘树苗种下,想来再也看不到它们长大结果了。
苏轼从黄州北上,途中专程到金陵拜见隐居了八九年的王安石。
那天,王安石骑着一头驴去码头迎接苏轼。苏轼连帽子都没戴,就上岸对王安石说:“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大笑:“礼岂为我辈设哉!”这句话出自《世说新语》,是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说的。被罢相彻底离开政坛后,王安石的思想变得颇为开通。苏轼这时倒不忘怼王安石:“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意思是,他们在政治上不是一路人。
虽然在政治见解上存在分歧,但不妨碍同时代的两颗巨星保持私人友谊。在金陵期间,两人放下变法之争,相约同游山水,多次作诗唱和。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这时的苏轼,还打算“买田金陵”,跟王安石一起归隐钟山。尽管后来未能如愿,但此时此地,苏轼的心境是真的。他意识到自己应该像王安石一样,尽早抽身隐退。
所以,苏轼并不着急到汝州去。他给宋神宗上了一个表,说明因“资用罄竭,去汝(州)尚远,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来得到批准。
没多久,宋神宗驾崩,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退隐洛阳著书长达17年的司马光,重新获起用为相,新党势力被全面压制。朝局风云突变。
苏轼很快被召还朝,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在这场名为“元祐更化”的政治变动中,大权在握的司马光在病中坚持尽废新法,甚至最后几天上朝都为此忙得不可开交。而苏轼遇事不吐不快的个性再次展现出来,他建议朝廷权衡利弊,保留变法中有益的部分。他本人支持保留免役法,废除青苗法。司马光却不听劝告。
王安石原本对朝中的变化默默无语,直到免役法被司马光所废,才老泪纵横地哀叹道:“就连免役法也要废除吗?我跟先帝可是研究了整整两年才推行,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全了。”1086年,元祐元年,王安石与司马光先后病逝,而变法引发的内耗与纷争远未休止。
朝廷上慢慢衍生出洛党、朔党、蜀党三党之争。北宋政坛对蜀人一直怀有偏见。苏轼在世时名声已经很盛,但他从来没有机会真正操持权柄。每当他被列为宰辅的人选时,朝廷言官就会以“蜀人太盛”进行阻止。苏轼虽然被当成“蜀党”领袖,但高太后很了解苏轼、苏辙兄弟,说:“我知道,你兄弟二人在朝自来孤立。”

▲大宋朝堂党争不止。图源:电视剧截屏
回帝都汴京四年,不堪政争的苏轼屡次请退,终于在1089年获准外调杭州知州,离开了是非之地。
苏轼虽以文学大家扬名,但他是个实干型的官员,受不了朝廷上冗长而没意义的政争。做一方父母官,为百姓干实事,反而是他最舒服的去处。从政以来,他做过密州、徐州、湖州、杭州等多个地方的一把手,每到一地,革新除弊,因法便民,兴修水利,应对灾害,都留下了相当好的口碑。
宋人笔记记载,苏轼在杭州为官期间,经常在西湖边上办公,早晨从涌金门泛舟而来,中午到普安院吃饭,于冷泉亭据案断决,处理公文时“落笔如风雨”,傍晚则乘马以归。
他关心民瘼,勤政为民,对百姓怀有深深的同情心和同理心。这样的地方官,即便没有那些经典诗词的加持,也一定会留名史册。
出任杭州知州后,当地大旱歉收,并爆发瘟疫,《宋史》记载“饥疫并作”。苏轼上书朝廷,请求减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又组织赈济灾民。面对疫情,他拿出了一个名叫“圣散子”的药方。那是他从蜀中故人巢谷那里拿到的秘方。这一秘方对于救急,疗效奇佳,巢谷秘不示人,连亲生儿子都不肯传授。后来,他实在拗不过苏轼的纠缠,把苏轼带到江边,要他对着江水发毒誓,绝不传给他人。然后,才把秘方交给苏轼。但面对百姓生死,苏轼已经顾不得他的誓言,他公开了这个秘方,并在街头支起大锅,煎熬汤剂,救人无数。
在这场疫病中,苏轼还从公款里拨出二千缗钱,并带头捐出五十两黄金,设立了“安乐坊”,作为救济贫病之人的公办医疗机构。安乐坊后来成为北宋安济坊的原型。
史载,苏轼在杭州做了许多实事,杭州人感激他的恩德,家家挂有其画像,“饮食必祝”。
苏轼去世后,杭州一名老僧回忆,他年轻时在寿星院出家,夏天常常看见苏轼一个人赤脚上山。苏轼会向他借一把躺椅,搬到竹林下,脱下袍子,赤背在午后的阳光下小睡。突然,他发现苏轼的背上有七颗黑痣,像北斗七星一样排列。老僧人说,这说明苏轼是到人间做客的神仙。
“神仙”是来做事,也是来历劫的。
高太后去世后,宋哲宗亲政,新党再度得势。1094年,绍圣元年,58岁的苏轼被贬至惠州。
在惠州,苏轼继续往美食家的方向进修。当年在黄州时,他就因为穷而独创了猪肉的做法,成为后世流传的“东坡肉”的创始人。如今,他又成了所谓的“羊蝎子之父”。
因为是被贬斥的罪官,苏轼在惠州没有资格与当地权贵争抢好的羊肉。他私下嘱咐杀羊的人,给他留下没人要的羊脊骨,在这些骨头之间也有一点羊肉。取回家后,他先将羊脊骨彻底煮透,再用酒浇在骨头上,点盐少许,用火烘烤,等待骨肉微焦,再吃。他终日在羊脊骨间摘剔碎肉,自称就像吃海鲜一样美味。
他在给弟弟苏辙的信中调侃对方,老弟啊,你生活优渥,饱食好羊肉,把牙齿都陷进去了也碰不到羊骨头,怎么能明白这种美味呢?在信末,他又说,这种吃法是不错,只是每次自己把骨头上的肉剔光了,围在身边的几只狗都很不开心。
苏轼在惠州还爱上了岭南佳果——荔枝。他跟儿子开玩笑说,千万别让自己的政敌知道岭南有荔枝,不然他们都会跑过来跟他抢着吃。
1097年,绍圣四年,苏轼被贬到了极远极荒凉的海南岛儋州。
长子苏迈来送别,苏轼把后事交代得一清二楚,如同永别。他决定到海南后,为自己做一口棺材。到了海南,才知道当地人根本不用棺材,他们在长木上凿出臼穴,人活着用来存米,人死了就放尸体。
一次,他在田垄上放歌而行,一个老妇人迎面走来,对他说:“先生从前一定富贵,不过,都是一场梦罢了。”他听后,大惊。
他常常站在海边,看海天苍茫,料定自己应该不可能活着离开这座孤岛了。不过,他后来转念一想,这个世界上的人,不都身处在大海的包围之中吗?而自己像一只蚂蚁,跌入一个小水洼,就以为落入了大海,于是慌慌张张爬上一片草叶,不知自己会漂向何方。可是,用不了多久,阳光照射,水洼干涸,小蚂蚁就生还了,见到同类,还哭着说:“我差点就再也见不到你了。”这只蚂蚁很可笑,但个人在天地间的悲哀,何尝不是如此?
在孤岛上活通透了的苏轼,还是得到了命运的最后一丝眷顾——1100年,随着宋哲宗的病逝,朝局再起变化,苏轼获准北归,活着离开了海南。
第二年正月,苏轼一家北归途中,在大庾岭上一间小店休憩,有个老翁问跟随的仆人:“官是谁?”
“苏尚书。”
“是苏子瞻吗?”
“是的。”
老翁上前向苏轼作揖说:“我听说有人千方百计陷害您,而今北归了,真是天佑善人。”
苏轼笑而谢之,随即题诗店壁:
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
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李一冰在《苏东坡新传》中说,苏轼历劫归来,最大的庆幸,是他平生一片刚直的孤忠,而今大白于世。一切污蔑和猜忌的浮云已经吹散,则天上一轮孤月,也当为人所共见了。“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
越过南岭,经赣江入长江。苏轼想着等儿子们举家到齐,就搬往河南许昌,去跟弟弟苏辙同住,实现他们年轻时许下的夜雨对床的约定。但北方政局突然大变,新党曾布开始专权。许昌临近帝都,苏轼担心到那里又起是非,故无奈写信托人转告苏辙:“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乎!亦不知天果于兄弟终不相聚乎?”
船到仪真(今江苏仪征)时,苏轼曾跟米芾见了一面。米芾把他珍藏的两幅书法交给苏轼,请他写跋语。但仅仅两天后,苏轼就瘴毒大作,猛泻不止。过了数日,病情一点也没有减轻,这时的苏轼隐约有不好的预感,他在信里嘱托弟弟说,我死后,把我葬在嵩山下,请你来为我写墓志铭。苏辙接到这封信,痛哭不已。

▲苏辙画像。图源:网络
到了常州,苏轼停下了他的旅程。他病了50多天,已经进入弥留之际。
他对三个儿子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我一生没做亏心事,不会下地狱的。
又说,我死时,千万不要哭泣,让我坦然化去。
长子苏迈询问后事,苏轼没有回应,溘然而逝。这一天是北宋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公元1101年8月24日。宋人笔记记载,苏轼死后,他眉山老家的彭老山,草木恢复了繁茂。天地灵秀之气重归于天地。
在最后生病之前,苏轼刚刚给自己写了四行诗,作为一生的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不是无神论者,但他在每一段见鬼的人生阶段,慢慢修炼得通透而无所畏惧。黄州、惠州、儋州,是他的三段贬谪经历,是他的政敌与常人眼中的黑暗阶段,但苏轼不这么认为。
不是熬过这些黑暗的时光,就会过上好的人生;而是,与这些黑暗的时光共处,这本来就是人的一生。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尽管苏轼已经去世900多年,但这只飞鸿,并未如他所担忧的那样消失无痕:他和它依然活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