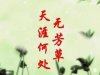时光是一壶慢慢熬煮的茶,前半生煮的是浓烈的执念,后半生滤的是清淡的释然。
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放不下的人、解不开的结,在岁月的浸泡里,渐渐化作轻描淡写。
不是遗忘,而是与过往和解;不是妥协,而是把遗憾酿成了温柔。
今日推荐十首诗词给你,藏着“拿得起”的勇气,更藏着“放得下”的通透。
千百年后,仍能从字句中读懂:释然,是人生最温柔的底色。
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宋神宗元丰五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第三年。春日与友人出游遇雨,众人狼狈避雨,他却拄竹杖、穿草鞋,在雨中缓步吟咏。雨打树叶的喧嚣、料峭春风的寒意,在他眼中皆为寻常。
一生本就常在“烟雨”中漂泊,何惧这一时风雨。
“竹杖芒鞋轻胜马”藏着放下的通透。曾经的他,是朝堂上意气风发的才子,渴望建功立业,贬谪的打击却让他看清:功名利禄不过身外之物,竹杖芒鞋的自在,远胜宝马雕车。“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是释然的极致。回头望过往狼狈,已分不清是风雨还是晴天,心湖平静后,外界起伏便再难扰心境。
这份通透,藏着前半生“拿得起”的豪情,也藏着后半生“放得下”的从容。
陶渊明《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东晋末年,官场黑暗,陶渊明几番出仕又辞官。他曾渴望在朝堂实现抱负,却终究看不惯世俗阿谀奉承,最终归隐柴桑乡间,筑茅屋而居,每日与菊花、南山为伴,远离车马喧嚣,只剩内心平静。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释然,是与仕途的和解。前半生,他曾“拿得起”济世安民的理想,在官场挣扎;后半生,他“放得下”功名利禄的执念,明白真正的自由不在朝堂,而在内心安宁。弯腰采菊时,不经意抬头望见南山,山气、飞鸟、落日皆成生命馈赠,所有遗憾与不甘,都化作“欲辨已忘言”的淡然。这份淡然,不是逃避,而是看清人生“真意”——比起追名逐利,内心丰盈才是永恒。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唐敬宗宝历二年,刘禹锡被贬谪二十三年后归洛阳。在扬州与白居易相会,白居易写诗叹其遭遇,满是同情惋惜,他却写下此诗,无半句抱怨,唯有对过往的释然。二十三年巴山楚水的凄凉,如一场漫长的梦,醒来时,早已不是当年少年郎。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最豁达的释然。他以“沉舟”“病树”自比,坦然承认过往失意落魄,却也看见千帆竞发、万木逢春的生机——即便自身落后,世界依旧向前,何必沉溺过去遗憾。前半生,他“拿得起”革新变法的勇气,为理想不惜得罪权贵;后半生,他“放得下”对命运的怨怼,明白人生总有起伏,低谷时仍能看见希望,才是真通透。
王维《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王维中年后,历经官场浮沉,见证安史之乱动荡。曾经的他,亦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志,晚年却选择隐居终南山,潜心向佛,在山水间寻内心平静。每日独自出游,兴致所至便随意行走,无目的地,也无时间表。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释然,是与命运的和解。走到溪水尽头,本是无路可走,他却不慌不忙坐下,看云朵悠悠升起。
人生亦然,看似绝境之处,换个角度便有新风景。前半生,他“拿得起”兼济天下的抱负,在朝堂与山水间徘徊;后半生,他“放得下”对仕途的执念,明白“胜事空自知”的独处,远胜官场热闹。
这份和解,不是消极退守,而是历经风雨后,学会随遇而安。
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唐玄宗天宝末年,李白因得罪权贵被排挤出长安,四处漫游。在宣州与族叔李云分别时,怀才不遇的愤懑满溢——昨日时光难留,今日烦恼挥之不去,抽刀断水、举杯消愁皆徒劳,这份愤懑却在诗尾化作释然。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是最洒脱的放下。前半生,李白“拿得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渴望在朝堂施展才华,现实打击却让他明白:非所有努力皆有回报,非所有理想皆能实现。既然“不称意”,不如“散发弄扁舟”,挣脱世俗束缚,在江湖寻自由。
这份洒脱,藏着对现实的无奈,更藏着对人生的通透。与其在烦恼中沉沦,不如放下执念,奔赴更广阔天地。

黄庭坚《鹧鸪天・黄菊枝头生晓寒》
黄菊枝头生晓寒。人生莫放酒杯干。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
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
黄庭坚晚年被贬宜州,生活困顿,却仍保持乐观。深秋清晨,黄菊枝头带寒,他劝自己“人生莫放酒杯干”,风雨中吹笛,醉里簪花,全然不在乎旁人眼光。二十年来,见惯富贵如浮云起落,尝尽人生酸甜苦辣,早已学会与生活和解。
“富贵浮云,俯仰流年二十春”的释然,是对名利的看淡。前半生,他“拿得起”文人风骨,在朝堂坚守原则,却因此屡遭贬谪;后半生,他“放得下”对富贵的渴望,明白“身健在,且加餐”才是根本,“舞裙歌板尽清欢”才是生活真谛。黄花与白发相牵,是岁月痕迹,也是释然见证。不在乎旁人“冷眼看”,只珍视当下快乐。这份看淡,藏着历经沧桑后的从容,也藏着对生活最朴素的热爱。
陆游《书愤・其一》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陆游一生渴望收复中原,年轻时北望中原,意气风发,曾在瓜洲渡、大散关浴血奋战,自比“塞上长城”,立志保卫国家。直至晚年,才发现理想难抵现实残酷,中原未复,自身已两鬓斑白,壮志未酬。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的释然,是与理想的和解。前半生,他“拿得起”收复河山的壮志,将一生心血倾注抗金事业;后半生,他“放得下”对“必成”的执念,明白有些理想即便自身无法实现,仍值得坚守。推崇诸葛亮《出师表》,非因遗憾,而是敬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这份和解,不是放弃,而是将理想化作传承的信念。即便老去,仍信有后人完成未竟事业。
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辛弃疾一生以抗金复国为己任,却因南宋朝廷苟且偷安,始终难展抱负。年轻时不懂真正的愁,为写新词故作忧愁;晚年历经官场排挤、理想破灭,才尝尽愁的真味,这份愁绪,却再也说不出口。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的释然,是对愁绪的放下。前半生,他“拿得起”抗金复国的豪情,为理想奔走呼号,屡遭打击仍不放弃;后半生,他“放得下”对“诉说”的执念,明白有些愁绪说亦无用,不如化作一句“天凉好个秋”,将遗憾与愤懑藏进对秋日的感叹。
这份放下,不是麻木,而是历经风霜后的通透。愁到极致,反倒学会平静,只因知晓生活仍要继续。

白居易《醉赠刘二十八使君》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白居易与刘禹锡为挚友,二人皆因革新运动被贬多年。刘禹锡被贬二十三年后归洛阳,白居易设宴相迎,席间写下此诗,叹其才华与遭遇。刘禹锡才华横溢,被誉为“诗国手”,却因才华遭妒,一生仕途坎坷,满朝官员皆升迁,唯有他在岁月中蹉跎。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的释然,是对命运的接纳。前半生,刘禹锡“拿得起”革新变法的勇气,为改变国家积弊不惜得罪权贵;后半生,他“放得下”对仕途的执念,明白“亦知合被才名折”,才华带来荣耀,也带来磨难。即便如此,他仍无抱怨,与白居易饮酒作乐,在诗酒中寻慰藉。
这份接纳,藏着对现实的无奈,更藏着对人生的豁达。无法改变命运,便接纳命运安排,在寂寞中坚守才华。
李清照《鹧鸪天・桂花》
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梅定妒,菊应羞,画阑开处冠中秋。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
靖康之变后,李清照人生剧变,丈夫病逝,金石文物遗失,独自颠沛流离。晚年见惯世间繁华与落魄,尝尽人生悲欢离合,赏桂花时写下此诗,赞其淡雅清香。
“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的释然,是对自我的接纳。前半生,她“拿得起”对爱情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曾有“赌书泼茶”的美好时光;后半生,她“放得下”对过往的怀念,明白真正的美好无需外在颜色衬托,如桂花般,即便颜色暗淡,仍是“花中第一流”。批评屈原未将桂花写入《离骚》“无情思”,实则是赞桂花独特,亦是肯定自我价值。
即便历经磨难,仍要做最好的自己。这份接纳,藏着对过往的遗憾,更藏着对自我的珍视。

这十首诗词,虽藏着十种不同的释然,但内核却一脉相承:前半生,怀勇气“拿得起”理想、爱情、执念;后半生,携通透“放得下”遗憾、不甘、怨怼。
不是忘记过往,而是将过往酿成岁月的酒,淡而回甘;不是放弃追求,而是将追求化作内心的平静,从容前行。
人生如旅,前半程忙着赶路,想抓住所有风景;后半程才懂,有些风景注定错过,有些遗憾注定留下,而释然,便是学会与这些错过和遗憾温柔相处。
如苏轼的“一蓑烟雨任平生”,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诗词中的释然跨越千年,静静诉说:真正的强大,从非从不遗憾,而是遗憾过后,仍能笑着走向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