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社会的反日情绪达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高峰,且呈现出明显的非理性、极端化特征。从打砸日系汽车、集体抵制日货的社会事件,到一些地方市民因穿日本和服而遭受网暴和公开羞辱,再到媒体对任何“酷似”日本元素的锱铢必较(如河南《大河报》对武汉大学座椅标签的炒作),最后到令人震惊的苏州刺杀日本小学生事件,种种现象表明,一股强大且极具破坏力的工具化民族主义浪潮正在中国民间涌动。
这种情绪,既非纯粹的民间自发,更非对复杂历史真相的深刻反思,而是中共长期推行仇恨教育、意识形态宣传,特别是充斥荧幕的“抗日神剧”所种下的恶果。这些神剧通过夸张、娱乐化甚至科幻化的剧情(如“手撕鬼子”、“子弹拐弯”),不仅简化了残酷的战争史,更使年轻一代对历史产生了一种认知偏差和廉价的胜利感。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在一个强调对外开放和全球合作的时代,这种情绪反而日益高涨,并屡屡以暴力和非理性的方式爆发?
本文认为,中国当前高涨的民间反日情绪,并非单纯的历史仇恨延续,而是中共在经济下行、社会矛盾尖锐时,通过官方默许、媒体渲染和意识形态教育,将其作为转移国内压力的“屡试不爽的武器”。这种策略在政治学和社会心理学中可以被称为“替罪羊理论”(Scapegoating Theory):当统治者无法解决内部的结构性问题时,便会引导公众将对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和生活不安全感的不满和愤怒,投射到一个外部的、安全的目标上——即日本,以释放巨大的社会张力,并达成统治合法性的再巩固。探究这一现象,我们必须先审视中日关系史上那个被刻意淡忘的“蜜月期”,以及日本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巨大且无法回避的影响。
一、历史的巨大反差——从“蜜月期”到“冰点”的急剧转折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日关系曾达到一个空前的“蜜月期”,友好与学习是当时中国上下的主旋律。这与今天的紧张气氛构成了巨大的历史反差。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共高层一度将日本视为学习的典范和获取资金技术的重要来源。实用主义是这一阶段对日态度的核心。
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1978年,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日本。他不仅亲自乘坐了著名的新干线,更是前往参观了松下电器的工厂。邓小平对日本现代化成就的惊叹,成为了中国高层态度的缩影。他曾感叹:“我知道什么是现代化了!”官方宣传基调明确:要放下意识形态争执,学习日本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学习”基调。随后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则积极推动对华合作,奠定了日本对中国第一批现代化项目的关键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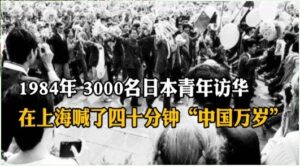
这一时期的民间和官方交流深度,使得中日两国人民互相对对方的好感度一度到达了80%以上。在文化和经济上,日本的渗透和影响力是全面的。日本的电影电视剧如《姿三四郎》、《血疑》、《排球女将》、《阿信》和电影《追捕》、《人证》曾风靡中国,其极高的收视率和引发的社会热议,帮助中国人建立了对日本普通民众的亲切感和具象认知,山口百惠、松坂庆子、真由美(中野良子)和栗原小卷等著名女星成了中国男人们心中的女神,而杜丘(高仓健),则成了中国女人心仪的标准男子汉。动漫产品如《聪明的一休》、《铁臂阿童木》、《花仙子》等,更成为中国一代青少年的文化启蒙。1980年9月,北京展览馆第一次举办大型音乐会,中央电视台破天荒地进行了现场直播,邀请的正是日本民谣歌手佐田雅志,那场演唱会让十几亿中国人知道了什么是通俗、民谣歌曲。
在外交方面,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邀请了三千名日本青年访问中国,这是中日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间交流活动之一。这次活动旨在推动民间友好,将双边关系推向顶峰,反映了 中共领导人希望通过“世代友好”来稳定中日关系的长期战略意图。
官方甚至集中力量拍摄了《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清凉寺的钟声》等一系列反映中日友好主题的电影,作为官方指导宣传的例证。为了纪念中日建交35周年,中国还拍摄了反映中日古代文化交流的16集电视连续剧《鉴真东渡》。
1980年,人民日报发表了解放军报社原副社长姚远方的通讯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讲述了聂荣臻战场救孤女的故事。次日,日本《读卖新闻》也在头版头条刊载了相关文章对此事进行报道,中国元帅人道主义救助战争孤儿的故事震动了日本社会。
1980年7月14日,当年的小姑娘美穗子应聂荣臻邀请,从日本来到北京。国内、国际媒体都以《日本女儿到中国寻亲,他的父亲是一位元帅》为题全程报道。这个动人的故事还写进了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简称苏教版)的中国小学六年级下册的课本。

在中共长期主导的“受害者”叙事下,日本在近代史上对中国的正面影响被系统性地忽视了。然而,历史事实是,日本曾是中国走出蒙昧、迈向现代化的关键跳板,其贡献是结构性的。
近代史上,包括孙中山、陈天华、宋教仁、鲁迅等在内的无数中国仁人志士都曾留学或避难日本。日本不仅是他们躲避清廷追捕的避风港,更是他们接触西方现代思想、学习科学知识、酝酿革命的重要场所。日本的教育体制,特别是弘文学院等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专门学校,为他们提供了学习西方思想的快速通道。这些“日漂”回国后,成为了中国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的骨干力量。可以说,没有日本,中国的近代革命和思想启蒙进程将面目全非。
这一影响更为深刻且普遍,它直接构成了当代中国人的现代知识体系。当代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许多词汇,并非直接来自西方,而是由日本学者从西方概念翻译后,再传入中国。这是一种“汉文化圈现代化的共振”。在政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乃至日常行政用语中,有近乎百分之七十的词汇来自日语或经由日语翻译。
这些“日货”包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派出所、警察、数学、物理、化学、哲学、经济、干部、服务、权利、义务、民主等等。如果按照极端反日逻辑,推行彻底的“抵制日货”,那么中国的现代知识体系将面临坍塌,中国人甚至可能无法说出一句完整、有内涵的现代汉语。这种文化上的巨大借用,恰恰说明了日本在近现代史上对中国知识体系构建的巨大作用,是任何“反日”宣传都无法抹杀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