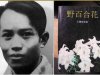1961年,我考进了北大中文系。北大那时实行五年制,还有六年的专业。一开学,杨晦主任就在迎新大会上讲,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里是培养学者的。当作家在我本不过一时兴到之意,无可无不可,那就不当算了,当个学者也蛮好。新同学中不少人本来是非要当作家不可的,有的还发表过小说或诗歌,这时全傻了眼,过了好长时间才回过神来,不得已只好准备当学者。
我很顺利地适应了这里的学习生活。当时名师如云,游国恩、王力、吴组缃、林庚、王瑶、彭兰、朱德熙、吴小如、陈贻焮诸先生都给我们上课。吴小如先生一年级给我们讲诗歌选和散文选,那些作品有若干是我先前读过的,但听他一讲才知道这里面还有许多奥妙,是我过去没有弄清楚或者根本没有想到的。稍后听彭兰、陈贻焮、赵齐平诸先生讲文学史,风格各异,又得到多方面的启迪。读文学作品只是认得那些字能讲出大意来远远不够,这里牵涉到文字、音韵、训诂,要研究文章的作者和时代,义理、考据、辞章,各种学问,一样也不能少。“学问是个无底洞啊”,我对这话有了新的体悟。那些年真的读了不少书,读得比较上路,同过去的囫囵吞枣乱读一气相比,颇有天壤之别。
北大特别自由,课外时间很多,图书馆里书太多了。在一个位置比较偏的分馆里可以借到线装书,一函只要一张卡,一次可以借出一堆来,记得有一回我去借《六十种曲》,特别带了一个大网袋去,费很大力气才运回三十二斋四楼的宿舍。星期天有各种讲座,随便听,最是开人胸襟,益人神智。有一次听图书馆梁思庄馆长开的讲座,才知道除了二十四史以外,还有“三通”以及扩大化的“九通”、“十通”,才知道什么叫“引得”以及它的妙用,才知道想查某一方面的资料如何着手才能比较快地到手。北大的课可以随便旁听,我听过几次讲版本、目录、校勘的课,大开了眼界,得到一个基本的线索以后不再去旁听,自己找书来看。我还到哲学系旁听过名家为高年级开的课,不少地方听不懂,提到的书没有读过或简直没有听说过,两节课听下来,完全坠入云雾。缺少先期知识准备则乱听无益,后来我不再乱听课了,一味听讲座,讲座不要求听众有多少知识准备,容易懂,收获大。做学问当然要多读书,但读书大有门道,过去其实尚未入门。知识的门类甚多,过去所知太窄,非大大扩展不可。
读得多了,听得多了,便发现同一作品、同一问题往往会有不同的分析不同的看法,有的相去甚远,有的差别细微,各有各的道理,为了得一究竟,常常苦思冥想,半躺在未名湖边草地上发呆。老师在课堂上也介绍一些学术界不同的意见,启发我们去思考。我曾经在一份为《北大人》写的小传中回忆那时的情形道:
在母校时,宿舍里几乎每晚都有清谈,上自国家大事,下至鸡毛蒜皮,无主题无旋律无所不谈,重点自然在文学,而文学中又课内课外古今中外阳春白雪下里巴人无所不谈,重点自然在课外。人人以未来的大学者自居,当仁不让,振振有辞,放言无忌,动辄抬杠。抬完了,相视而笑,莫逆于心,洗脚睡觉,明天再谈。尔后三十年间,此种魏晋式或五四式的盛会是没有了,令人思之如失恋者。只有等到老同学聚会时,才能略略重温旧梦,接着再谈,可惜头发渐白,世故渐多,而且行色匆匆,不免是叙旧存问多于无边际的纯学术讨论了。即使偶有讨论,也温文有余,生气不足,失去“火药味”。幸而杠还可以抬得起来,嗓门一高,儿女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意外,来相探视,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与当年相比,小巫而已。(《北大人》第三辑,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