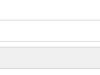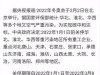图为示意图。(AAP Image/Darren England)
每逢“五一”、“十一”等长假,中国各地都会出现大规模“人从众”的景象。为刺激旅游消费,中共官方通过调休安排,使得假期延长至5~8天。然而,由于平日请假困难,部分企业甚至仍实行单休或“大小周”,民众的长途出行与返乡探亲需求被迫集中于法定长假之中。
今年中秋节与“十一”国庆假期合并,共达8天。但节前节后却需补班2天,引发大量网友在社交平台怨声载道,很多网友抱怨“假期不如不放”。
陆媒《财新》9月29日报导指出,中国公共假期分布不均,下半年假期稀少,加上调休补班,让劳动者的“假期获得感”大打折扣。
事实上,中国的长假制度本身就是出于拉动消费的考量。“五一”黄金周在2008年曾被取消,直到2019年才恢复为5天。当时新华社引述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刘思敏称,恢复长假“有利于促进消费,拉动内需”。
刘思敏称,3天左右的小长假不足以支撑远途旅游或长途探亲安排。正因如此,才会出现“五一”、“十一”、中国新年等少数长假集中出行的现象。
长假需求集中,还与中国劳动者长期缺乏日常休息直接相关。
根据人社部2020年数据,仅约六成劳动者能够落实带薪年休假,四成职工“有假休不到”。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显示,制造业职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达5.68天,不少企业仍实行单休或“大小周”制度。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近日的文章指出,中国居民普遍存在“休不够、休不好、休不到”的问题。
工作时长过长:中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约49小时,折算年工作时长约2500小时,高于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1717小时,也超过发展中国家墨西哥的2323小时。
闲暇时间偏短:2024年官方《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显示,中国居民日均闲暇时间仅3.5小时,远低于欧洲(平均5小时以上)、美国(4.7小时)、日本(4.6小时)。
2017年中共央视、国家统计局等联合发起的“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结果显示,深圳、广州、上海、北京居民每天的闲暇时间分别仅为1.9、2.0、2.1和2.3小时。
居民假期“休不够”,主要表现为带薪年假数量偏少。中国劳动者有5到15天带薪年假,平均年假为10天,低于法国25天、德国20天,也低于墨西哥(12-20天)、巴西(10-22天)、俄罗斯(至少28天)。
居民假期“休不好”,主要表现为公共假期分布不均、下半年偏少,调休补班让获得感打折。中国公共假期主要集中在上半年(9天),下半年数量偏少(4天),全民集中休假导致休假旅游体验感不佳,“人山人海”和交通拥堵已是假期常态。此外,调休后的持续工作导致劳动者身心俱疲,削弱了假期获得感,“假期天数不输人,调休凑假累垮人”的感受普遍存在。
放长假的结果,是全民同时出行,导致旅游体验感大幅下降。道路拥堵、景区爆满早已成为常态。今年“五一”期间,桂林漓江甚至上演了“船只堵塞”的罕见场景,被戏称为现代版“赤壁之战”。
《极目新闻》报导,10月1日假期第一天,全国各地迎来了出行客流高峰。有网友表示,堵堵堵!许多司机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开着开着就突然堵车了,只能一点点蹭着前行。车辆堆积得越来越多,逐渐蔓延到很远的后方,造成严重的堵车现象。
据百度地图大数据显示,十一假期全国高速平均拥堵里程较历史同期上升75.8%,景区、游乐场人流翻倍增长。
从去程情况看,由于十一出游与中秋探亲的车流叠加,假期首日出行强度增长突出,去程拥堵最高峰值出现在10月1日11:00,峰值为9109.28km,全国高速平均拥堵里程较历史同期上升50.1%。
拥有超40万粉丝的博主“老周”在社交平台写道:“出门旅游本来是为了放松,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比上班更苦、更累、更折磨人。”
中国的调休政策已经持续二十余年,几乎每到长假都会引发民众不满。“老周”指出,调休并非真正增加假期,而是“拆东墙补西墙”,把分散的休息日强行集中,造成全国“扎堆出行”的局面。
“老周”认为,问题不在于中国人口多,而在于“全社会统一放假”。以人口密度远高于中国的城市为例,新加坡每平方公里超8000人,北京仅1330人,上海约3900人。然而,新加坡和东京在假期期间极少出现中国式的“人山人海”。“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这个万恶的调休制度。”
那为什么中共不改革调修政策?“老周”表示,调休制度的逻辑不仅仅是刺激消费,这背后真正的原因并不只是刺激消费那么简单,它是一套被隐藏很深的社会控制机制。它在塑造官方叙事的同时,制造了民众“获得更多假期”的错觉。搞得好像是政府大发慈悲地在给人民提供了福利一样。实际上,劳动者的总休息时间并未增加,反而因补班而更加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