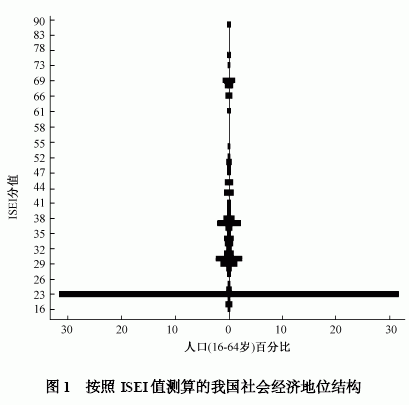想想你是谁:潜在购物者?夜猫子?还是特别喜欢某一类新闻的人?不过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如先想想你的身份到底是你自己决定的,还是算法决定的?
1.引子:标签
这篇文章可以先从我热爱户外的强者朋友巧大力开始讲起,三年前的某一天,大力告诉我,他在宿舍里提了一嘴登山鞋,几个小时后,他在每个APP上刷到的内容就全成了登山鞋。我说肯定不会这么离谱的,毕竟你天天买那些户外用品,算法记住你了,给你推两双鞋也是正常的。
不过到那天吃饭的时候,我就又陷入了思考。登山鞋也好,路线推荐也罢,看不见的系统肯定是把巧大力放进了“可能购买登山装备的人”的框架里,这个分类又会影响他之后看到什么、被推荐什么、更甚至在消费之外的选择。
当然,日光底下无新事,我们从小就在经历分类,上课的时候,好学生当了班长,差生坐在讲台的左右护法位置。诊断书上有健康和病人的分类。在政府文件里有公民和外国人的分类。人们用这个来管理世界。但同时,分类也在影响我们看待自己方式,我们可能会把被打上的标签变成自己的身份认同。
哲学家 Ian Hacking在书中写到,分类并不是静止的。他用ADHD来举例,提到当一个孩子被诊断为“过动症”的时候,他不只是被贴上标签,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循环:父母会改变对他的期待,老师会调整对他的教学方式,而他自己也可能开始以“过动症患者”的身份认识自己。这或许能说明,分类不只是反映现实,它们还在建构现实。
但在数位时代,这种建构的力量被大大放大了。算法、平台、数据库——所有的这些都在重新设计我们的社会现实,如果是这样的话,谁又有资格来定义我们是谁呢?
2.你觉得现实是天然的吗?
人类似乎有一种将事物归类的本能。我至今都没遇到过哪个不喜欢分类游戏的人。
我的朋友大多和我一样,我们喜欢分类游戏,大众一点的有星座,MBTI,小众一点有九型人格,8Values,我们会聊大家是哪一派,支持哪个政党,或者学习哪个专业,种种问题成了我们日常讨论的根基。
我记得我的朋友夜隼第一次测完MBTI后大喊,“这也太准了,我就是典型的 INFP”,另一个朋友就补充说,“对啊,我早就觉得你是,就你这个心思细腻加拖延,八九不离十”,轮到我测试,我测出来一个INFJ,大家又开始说“Luna你怎么可能是I人啊”。我本身不反感分类,因为这些分类带来一种轻松的归属感,让人觉得自己被看见了,也终归让人际交流多了一层话题。
不过,有时,我也总是担心这些标签会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当我告知一个人我有ADHD,别人或许会理解一些我的奇怪之处。比如,晚回复或者忘记回复消息的时候,打断别人说话的时候,或者跟不上别人说话的时候。这个标签可以让别人觉得我或许并非不尊重他们。但我也担心在学校或者公司里提到自己的特殊需求时,会被别人质疑工作能力,这些总给我带来压力。这些标签,伴随着对症状的解释,总是像影子一样,无论走到哪里都跟着我。所以有时候,纵使像我这样为自己的“神经多样性”特质骄傲的人,仍然会想要隐藏自己的身份。
这也是分类的力量。
Ian Hacking在书中提到,岩石和电子不会因为我们怎么称呼它们而改变,但人会。我总是会想,拥有一个诊断意味着什么,ADHD也好,自闭症谱系也好,诊断被记录在医疗档案里,进入家庭、学校和职场,也伴随着解释,父母需要改变期待,老师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教学,社会需要建立支持体系,同事和同学要与这样的特殊朋友相处、协作,但作为被诊断的人呢,他们也要将这样的标签纳入对自己的理解之中。失败的时候会怀疑是不是因为这个疾病,而成功的时候也会担心会不会下一次就做不到了,这也是压力。
星座和人格测验通常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轻松的身份游戏:我们可以选择相信,也可以把它当笑谈。而医学诊断却带有真正的后果。因此需要谨慎。一个医疗标签会影响教育资源分配、就业机会,影响一个人对未来的想像。它既可能带来帮助——帮助获得药物与策略,知道怎么更好地生活;也可能带来局限——一个潜在的“有问题”或“不可靠”的标签,因此甚至想要隐瞒。
所以有时候,当我们说“我是 ENFP”“我是天蝎座”“我是 ADHD患者”时,我们不只是描述自己,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一种社会为我们设计的镜像。而我真正害怕的是这些镜像会反过来塑造我们的行为。久而久之,就让我们真的开始活成了分类所描述的样子。但一个人是有很多面的。分类和标签让我们只看到一个人的一面。
我又想到一个案例,大约两个星期之前,我在Amnesty组织的一场关于难民议题的研讨会上,听到了一位分享者分享她在边境营地的经历。她说,当她问一位中年女性“你为什么来到这里”时,那位女人愣了一下,然后低声说:“因为我是个母亲。”这个回答并没有落在法律文件的任何一栏里。她不是“因为战争”或“因为政治迫害”才离开,只是因为在混乱中,她的孩子需要活下来。
我一时语塞。我又一次想到那些申请表和那些标签,一个人的身份可能是难民、寻求庇护者、非法移民。到后来又有了新的分类——“女性难民”。听起来更具人道关怀,能凸显女性在逃亡过程中遭遇的性别化暴力。但同时,它也把人们牢牢固定在一种形象里:脆弱、受害,需要被拯救。在海报上,“女性难民”往往是低垂着眼睛、怀里抱着孩子的身影。这种形象唤起同情,带来资金支持。但它是如此单一——一位女性难民,可能是一位学者,是一位律师,记者,甚至是企业主,其中有社会运动参与者,但也有躲避战争的年轻女性,来自加萨或乌克兰,但在分类之下,他们成了一个简单的符号,在女性难民的标签之外,她们首先是有复杂经历和多重身份的人。
我不禁思考,当我们讨论分类和分类困境时,我们应当意识到什么。我想到的答案是:分类是临时的,它是历史情境的产物。ADHD也好,寻求庇护者也好,女性难民也罢,它是一种处境,不是对一个人或者对人类经验的最终定义。
3.标签在数位时代
搜寻、点击、停留,每个微小的动作,在数位时代,都成了算法收集的对象,我尝试搜索平台的规则,却一无所获,平台没有告诉我它怎么解读一个人,但我思考他们给人打上的标签:购物欲强的用户、户外爱好者、偏向某一类新闻的读者。最后,你打开萤幕看到的世界,就是依照这些分类为你量身裁剪的。
这些分类和身份认同交织在一起,往往比我们意识到的更深入。当平台不断推送某类内容给你,你可能也会慢慢觉得,这就是“我”的一部分。我是喜欢某种音乐的人,我是容易被某些议题触动的人,我是这样一个“被定义”的使用者。
我想到最近的一个有趣案例,或许能解释分类是如何会自己长出生命,变成一种流行文化的。几个星期前,中国网红户晨风,因为“安卓人/苹果人”的分类梗一度爆红。他把“安卓人”说成低端、劣质,而“苹果人”代表高端、有品味。这个说法迅速传遍网络,网友们争相用它来调侃,甚至衍生出“安卓房”“苹果房”“苹果学历”之类的词。乍看之下这只是娱乐,但它实际上在建构一种身份边界——谁属于哪一边,意味着你属于什么样的阶层、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然而,当这种分类触及太敏感的社会神经时,它就不再只是笑谈了。因为挑动了消费与阶级的矛盾,户晨风最终被全网封禁,所有账号内容清空。分类在这里成了一种危险的语言,它既能吸引二百万人追随,也能在一夜之间让一个人彻底消失。
从医学诊断到算法,从 MBTI到“安卓人/苹果人”,我们的身份越来越像是一种不断被他人、被平台、被社会“重新编码”的东西。正如学者 Couldry和 Hepp所说,这就是“深度媒介化”:媒体与数字技术不再只是我们生活的背景,而是我们生活的基础环境。在这个环境里,我们以为自己在自由选择,其实早就被分类过无数次。
4.“谁定义我们”
有人相信,社会就像一门自然科学,能像研究星球或分子一样精确地研究人。这就是实证主义的世界观:他们会说,你的身份是可以被观察、测量、统计的,甚至能预测你将来会怎么做。就像今天的数据公司,把我们的点击和消费习惯输进模型,假设能用这些数字勾勒出“真实的你”。
但也有人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韦伯和后来的诠释学者们强调,人不是一个可以被数字化的机器,而是有意义和故事的存在。如果要理解一个人为什么这么做,就必须理解他所处的文化和语境。比如说,一个移民家庭孩子的“沉默”在统计表里可能只是“低参与度”,但对当事人来说,那可能是一种在陌生社会里自我保护的方式。这些人会告诉我们:要理解分类对人的影响,就要从人自己赋予行为的意义出发。
还有一些思想家,像马克思主义传统和后来的批判理论,他们更关心的是权力。他们会说:我们之所以被定义成这样或那样,并不是偶然,而是和谁握有权力、谁控制资源密切相关。当国家把人叫做“非法移民”,当平台把人标记为“高风险用户”,这些分类都不只是中立的描述,而是服务于某些结构的利益。
这些不同的声音,其实像是三种对“我们是谁”的回答:一种相信我们可以被量化;一种相信我们需要被理解;一种则提醒我们去看清分类背后的权力游戏。而我们今天生活在数位时代,这三种视角似乎同时都在发生:数据公司在量化我们,文化背景在影响我们,权力机制在规训我们。这也是为什么“谁定义了我们”这个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复杂。
5.如何处理这些隐形的建构
我们已经看到,分类无处不在,但如果我们想更仔细地理解这些分类是如何塑造我们的生活,该怎么办呢?
媒介研究者给出的答案是:去看文本,去听人们怎么说,去追查制度背后的结构。
例如,当一则新闻报导谈到“非法移民”时,这四个字本身就是带着态度的。它不仅是一个描述,更是在暗示:有些人是不合法的,不应该存在。研究者会把成百上千篇新闻收集起来,分析它们的用词、图像、叙事模式,看看一个群体是如何被“再现”出来的。这种工作听起来有点像拆解语言的显微镜,却能让我们看清新闻是怎样在不知不觉中建构现实。
有时,研究者会直接去和人聊天。以前我在做受众研究的时候,会邀请人们谈一下:你是怎么理解这则新闻的?当你看到某个广告时,你的感受是什么?有人可能会说“我不在乎”,但也有人会说“每次看到这样的报导,我就觉得自己被针对了”。这些访谈让我们明白,分类不只是媒体单向输出的,它还会被人们接受、抗拒、甚至重新诠释。
再往深处走,就要谈谈制度了。谈论制度像追查一个巨大的网络:谁拥有媒体?谁控制平台?谁决定算法的规则?研究者们需要翻阅公司年报、政策文件,或者分析社交平台的使用条款,去揭示权力是如何隐藏在“看不见的手”里。因为只有弄清这些,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声音被放大,有些声音则被压制。
媒介研究中非常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此,当你要拆掉一座巨大的房子时,你需要检查墙上的装饰(文本)、听听住户怎么抱怨或赞美(受众)、最后还要追溯设计图和建筑公司(制度)。只有这三方面放在一起,我们才能看清楚:我们的现实是如何一步步被建构出来的。
6.结语:如何夺回定义权
回到最初的问题:在数位时代,谁定义了我们是谁?
我想到那些诊断单上的结果,朋友圈签名上的MBTI,算法建立的用户画像,某个网络迷因(例如你是苹果人还是安卓人)。我们借着这些理解自己,理解别人,把我们困在角色里。直到我们意识到这些分类是历史的、偶然的、可以改变的,我们就能重新夺回一些定义权。我们看到LGBTQ+群体透过自我命名,把“病态”的标签转化为“骄傲”的身份;女性难民的议题让一个原本隐形的群体获得可见性;甚至在网络上,人们也常常透过反讽、恶搞来挑战既有的分类框架。
所以,也许问题的答案不是单一的“谁”,而是一场持续的角力:在我们和社会、媒体、平台之间,身份不断被定义、被质疑、被重写。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做的,或许就是保持清醒,去辨识那些看似自然却其实是人为的界线,并在可能的时候,勇敢地提出新的定义。
因为最后,被分类的人,也能成为改写分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