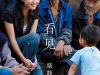说起目下文人的潦倒,刘东总会提到他楼下的一位名教授。那老者(《红楼梦》英译者杨宪益)寂寞时常把他叫去喝几盅,酒一下肚,便作"今昔对比",说他年轻时在大学教书,一月拿500光洋,必定每礼拜下馆子,教授们轮流作东,哪像今天这般寒碜?眼下的社会是决不肯再拿钱白养活读书人了。也难怪如今的学者再难做出胡适、陈寅恪那样的大学问。这是刘东常常感叹的。
我们闲谈中国的现代化,总感到它的命乖运蹇,或许同中国人总是太性急有关。胡适当年说过,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中国得的是慢性病,治这病的医生也不能太性急。知识分子要沉得住气,使不得虎医狼药,得耐心地给这个社会开一剂除病根的缓药。
这缓药便是树人之道。蔡元培办北京大学,其志向与功德之伟大,就在于要教出一个崭新的文明来。谁能不是教育家的精神之子?
"有一回我去北大演讲,就这详说过:我虽不是北大出身,却很为北大自豪。从陈独秀到毛泽东,哪个同北大没有关系?应当说,没有北大就没有共产党!"
刘东说得激动起来,把那张转椅压得吱吱响。
但"五四"以降,这副缓药便无人问津了,于是那病根过了70年也终于没能除掉,说不定还更沉重一些,这方面的话题,那些日子谈了许多,别的都记不清了,唯有刘东讲的一件小事,关于"五四"的史书中很少提及的,却再也忘不掉了。
‘当年蔡先生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遂安伯胡同。本来,5月2日是他最先召集北大学生班长和代表,把巴黎和会的噩耗告诉大家,号召学生奋起救国的。但在'五四'那天早上,他却匆匆赶到马神庙北大一院。他去干什么呢?如今谁也忌讳说这一层。原来他是去劝阻学生上街游行的!他说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已被视为异端,若再闹出事来,恐怕首先遭难。当然学生是不会听他劝阻的。’
这个细节太耐人寻味了。跟满清斗过的蔡元培还会怕北洋军阀吗?他是太爱他的北大了。他太知道"教国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图,还在学术'。他甚至认为学生因救国而牺牲学业,其损失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然而,即使像蔡元培这样的大智大勇者,在那时也难挽狂澜于既倒。启蒙与救亡的两难,真是中国之大惑。70年后回头想想,当初学生们要能在蔡先生门下多读点书,该有多好啊……….。
"五四"公案,海内外众说纷纭。有奉若开天辟地之壮举者,有抑启蒙而扬救亡者,有视之为"斩断中国传统"之大祸者,有上比拳乱下附红卫兵造反一锅熬者,差异之大,悬若霄壤;隔膜之深,宛如大洋。海外有雾里看花之朦胧,海内则有犹抱琵琶半遮面之暖昧。
这个真正属于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掀起的一场运动,由于初始的两难,也由于日后的迷失,更由于史学的硬拧,早已面目全非,离真实相去甚远矣。中国知识分子之可怜,不仅在于她的灵魂倍受扭曲,连她的"身世"也被篡改了。
我多么想去拜谒那些"五四"的英灵呵。年底,导演夏骏组成摄制组,我们一行六人,离京南下,去寻觅那早被遗忘的巨人们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