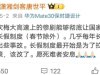象牙塔里的"学术蟑螂":从王灿抄袭事件看中国学术圈的道德溃堤
(一)系统性抄袭:一场精心策划的学术诈骗
2025年2月25日,复旦大学一纸"退站处理"通报,将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王灿推上学术审判台。这场始于台湾政治大学博士候选人叶沾的维权行动,撕开了中国顶尖学府光鲜外衣下的腐肉:自2022年至2024年,这位身兼武汉轻工大学副教授的"学术精英",竟以"复制粘贴"的方式剽窃四本台湾硕士论文,登上《文学评论》《戏曲研究》等顶级期刊。更令人震惊的是,抄袭者将学术不端升级为工业化操作——每篇论文不仅全文剽窃(含图表、注释),更跨越戏剧、文学、出版史等多个领域,俨然形成"代写-洗稿-发表"的黑色产业链。

这场抄袭狂欢中,王灿展现出惊人的"学术效率":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听觉传播媒介对近现代京剧美学的影响》被改头换面成《听觉复制时代的新声》,彰化师范大学《黄庭坚读书诗研究》摇身变为《阅读史视野下的宋代士人与读书》,台湾大学非虚构写作研究经"学术整容"后登上大陆顶级期刊。这种跨学科、跨地域的抄袭布局,已超出普通学术不端的范畴,暴露出精心设计的学术诈骗本质。
(二)监管失守:从期刊到高校的集体沦陷
当四篇"洗稿论文"轻易突破C刊防线,中国学术界的审查机制已然形同虚设。《戏曲研究》等编辑部坦言:比对系统未纳入台湾学位论文数据库,使得台湾研究成果沦为剽窃重灾区。这种技术漏洞背后,是学术共同体对边缘学术成果的制度性歧视——当大陆期刊将台湾论文视作"学术飞地",便为投机者创造了完美的犯罪空间。

更讽刺的是,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在接到举报后的应对堪称"官僚主义范本":12月2日举报,4日启动调查,26日仍在调查,次年1月8日才确认违规,最终处理结果拖延至2月25日公布。这种"挤牙膏"式的处理节奏,与其说是审慎调查,不如说是为涉事者争取"软着陆"时间。在此期间,涉事者仍能向受害者发送"情绪勒索"邮件,试图私了,可见学术权力对违规者的暧昧庇护。
(三)制度之癌:量化考核催生的学术怪物
王灿的"成功路径"折射出中国学术评价体系的深度畸变。在"非升即走"的生存压力下,武汉轻工大学将"首投C刊"作为职称晋升硬指标,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对"学术成果"的盲目崇拜,共同构建了滋生学术蟑螂的温床。当学术价值被简化为期刊目录上的字母符号,论文写作便异化为"学术裁缝"的拼贴游戏。
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导致抄袭行为呈现组织化特征。王灿团队深谙学术生产"潜规则":选择台湾硕士论文既规避查重风险,又满足C刊对"理论深度"的病态追求;跨学科抄袭既能制造"学术通才"假象,又可分散被揭发风险。当学术不端演变为精密算计的"风险投资",所谓的学术理想早已沦为利益博弈的筹码。
(四)两岸镜像:学术殖民主义的知识霸凌
此次抄袭事件暴露出两岸学术交流中的结构性暴力。抄袭者利用台湾学界在数字平台建设上的滞后性,将硕士论文这种"学术半成品"转化为大陆职称晋升的垫脚石。这种知识掠夺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学术殖民主义——当大陆学者可以肆意剽窃台湾研究成果而不受惩戒,所谓的"学术共同体"不过是强者逻辑支配下的知识霸权。
更值得警惕的是抄袭者的心理机制:王灿在邮件中称"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种将抄袭美化为"学术失误"的话术,折射出对台湾学术成果的制度性轻视。当大陆学术体系将台湾论文排除在学术伦理保护范围之外,实质上是构建了等级化的知识价值体系。

(五)破局之路:重建学术伦理的三重变革
要根治学术蟑螂的滋生,需要制度、技术、文化的三重革新。首先必须打破"唯C刊论"的考核体系,建立代表作评审、学术贡献评估等多元评价机制。其次要构建涵盖港澳台地区的一体化查重系统,将台湾硕博论文纳入学术诚信保护网络。更重要的是重塑学术伦理,将"引注规范"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让年轻学者理解:真正的学术尊严不在于期刊目录的字母,而在于对知识生产的敬畏。
复旦大学处理王灿事件时"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姿态,恰是当前学术监管困局的缩影。当学术不端的处理仍停留在"割席自保"层面,而非推动系统性改革,那么今日倒下一个王灿,明日还会涌现无数个"李灿""张灿"。唯有将学术反腐从个案处理升级为制度重建,才能阻止中国学术界在量化迷途中继续堕落。

象牙塔不应成为学术蟑螂的庇护所。王灿事件既是警钟,也是试金石——检验的不仅是复旦大学的学术良知,更是整个中国学术界自我净化的勇气。当抄袭者可以戴着"博士后"的光环招摇过市,当台湾学术成果仍被视为可以随意攫取的公共资源,所谓"双一流"建设终将沦为学术泡沫堆砌的海市蜃楼。重建学术伦理,需要的不是又一场运动式整顿,而是每个学术共同体成员对知识尊严的坚守与捍卫。
举报信全文
联合声明
本人叶霑,现为国立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候选人,2024年12月陆续发现本人及另外三本台湾的硕士论文,遭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研究员、武汉轻工业大学副教授王灿的恶意抄袭。经向各期刊及抄袭者所属单位的申诉检举,目前已大致得到正面的结果。我和另外两位受害者(张桓溢、王秀如)共同想向台湾研究生们,说明此一“系统性”抄袭的事件,警示各位的论文也可能(已经或即将)遭受抄袭,并分享我们申诉的过程,以供不时之需。
(一)抄袭梗概
本人叶霑于2024年12月2日发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期刊第130辑(2024年7月)刊载的王灿〈听觉复制时代的“新声”:民国时期京剧广播及其收听〉一文,几乎全文(含注脚的每一个字)抄袭本人之硕士论文《听觉传播媒介对近现代京剧美学的影响:以唱片、广播为讨论核心(1903-1940)》(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硕士论文,2020年)。
抄袭者王灿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研究员,亦为武汉轻工业大学副教授,博士学位似在南京大学取得。尤为令人震惊且愤怒的是,本人及友人陆续发现王灿自2022年至2024年期间,至少有四篇学术论文,几乎全文抄袭了四本台湾的硕士论文,且多数发表于中国大陆各大顶级期刊(俗称“C刊”)者。四篇抄袭文,以及被抄袭的硕论,列表于下方。
王灿四篇论文皆是“一字不漏”、“包含注脚”甚至“连同图表”的恶意抄袭,一次也不曾提及所抄袭之原著,已构成极为严重的学术不端。而在短短两年内高达四次的恶意抄袭,且以此获取复旦大学、武汉轻工业大学的学术工作机会,不仅是对多位原著者研究成果的重大侵害,更是对人文学术圈的蓄意诈欺。
王灿《“三重摹创”视野下非虚构写作的实践图式探究》,《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
抄袭自张桓溢:《现实的摹创与中介:论台湾非虚构写作的翻译、实践与理论》,台湾大学文学院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19年6月。
王灿《阅读史视野下的宋代士人与读书——以黄庭坚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出版史研究》2024年第3期。
抄袭自王秀如:《黄庭坚读书诗研究》,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国语文教学硕士班硕士论文,2010年6月。
前言、结论部分,又抄袭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员2006年期刊。(因尚未获得受害者之联络回复,故在此不公开受害者姓名与著作名称。)
王灿《听觉复制时代的“新声”:民国时期京剧广播及其收听》,《戏曲研究》第130辑,2024年7月。
抄袭自叶霑:《听觉传播媒介对近现代京剧美学的影响:以唱片、广播为讨论核心(1903-1940)》,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2020年6月。
王灿《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抗战时期边疆艺术调查研究──以贵州民间艺术采集团为中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9期。
抄袭自中央大学艺术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16年1月。(因尚未获得受害者之联络回复,故在此不公开受害者姓名与著作名称。)
(二)抄袭申诉处理
本人在2024年12月5日前透过各校系办转告其他受害者相关状况。面向各大期刊的撤稿要求,我们是向各刊物的信箱直接反映,其中《文学评论》并无公开信箱,则是拨打跨洋电话给编辑部反映。本人及所有抄袭者在此由衷感谢《戏曲研究》、《中国出版史研究》、《文学评论》编辑部已核实抄袭,并应允撤稿,且在下一期纸本刊物出版时,刊登撤稿声明。
另外,考量到抄袭者所属的学术机构,以复旦大学更具学术声望,当不致于轻率吃案。因此本人于12月2日首次向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举报王灿抄袭行径,分别于12月4日获得“开启调查”、26日获得“尚在调查”、1月8日获得“学术不端情况属实,移交有关部门据条例执行”之回复。具体执行结果如何,本人未再追问。再者,由于本人需要兼顾工作与学业,向来繁忙如无头苍蝇,故尚未匀出时间向武汉轻工业大学举报王灿,他是否仍留在该校担任“校内首度投上C刊的(副)教授”,我亦不得而知。
(三)台湾学位论文被“系统性”抄袭
四篇被抄袭之学位论文领域分散,遍及台湾大学台文所、台湾师范大学国文所、彰化师范大学国文所及中央大学艺术所。领域跨及当代台湾非虚构写作、近现代京剧研究、北宋阅读史、边疆艺术研究等。由于抄袭者本人的研究领域似为新闻学/媒介研究,但抄袭的论文又跨越多个领域,本人高度怀疑抄袭者可能是透过“购买”的方式,雇请各领域的熟悉者恶意对“台湾学位论文”进行“代抄服务”。
同时,四篇被抄袭之学位论文,都将全文公开于国家图书馆建置的“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因此抄袭者可以轻易透过网络取得文本。中国《戏曲研究》等期刊的编辑部也向我们表示,他们的论文抄袭比对系统,尚未纳入台湾的学位论文,因此学位论文系统反而成为不肖份子钻漏洞的工具。我们理解此系统是本于学术交流互惠的美意而创建,但仍希望台湾研究生的心血能被保护。
(四)抄袭者的情绪勒索
尽管期刊编辑部、乃至复旦大学,都还算愿意处理此事。然而在处理过程中,本人信箱曾在未经同意的前提下,为抄袭者王灿获取。王灿分别于2024年12月4、19、25日连续写了三封骚扰信件给本人:
第一封信中附上高血压病例,主张因为身体健康关系,且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抄袭”,因此“需要”本人原谅。
第二封信中声称“已离开学术单位”,感谢本人的举报,祝福本人“未来都好”。
第三封信声称本人收到信件时,他“已离开人世”,希望本人“未来都好,并不要对内地产生不好的想法。”(引文皆按信件原文)
本人在此期间从未回复王灿信件,亦与王灿没有任何交流,因全体受害者并不需要王灿私下的道歉,仅要求各大期刊及学术单位公开且正式的声明,以维护受害者最基本的权益。我们深知生命可贵,在接获王灿第三封自杀通知信件时,立即通报复旦大学,请他们关心这位博士后研究者的身心状况。复旦大学于12月26日回复,告知“被举报人目前尚好”、“案件尚在调查”。
(五)总结
所有无辜的受害者,划清与抄袭者王灿毫无必要之人情纠缠,包含他个人的疾病、经济状况、职涯发展或任何形式之自杀、自伤行为。并严禁王灿或其相关人等私下骚扰本人,要求本人“转达受害者”那些“立意扭曲、言词模糊、内容真假难测,毫无逻辑而令人不适”的道歉。
向台湾所有文史哲、艺术学界之研究生,提供一个血泪经验,希望所有研究生自此以后务必留意自己的论文(尤其是学位论文)是否被熟知中国大陆期刊查重系统疏漏之不肖者恶意抄袭贩售,成为大型不肖商业活动下的牺牲。
和台湾文史哲、艺术学界之研究生分享一个向中国期刊编辑部提出诉求的具体经验。
本人在此衷心感谢所有师长、至亲及挚友第一时间的帮助。因考量未必所有师长亲朋都愿意具名,在此请容许本人不一一列名致谢。同时也感谢愿意即时、妥善且完整善后的各大期刊编辑部。
作为一名没没无闻、无权无势更无钱的人文科系博士生,如果没有两岸的师长在繁忙中不辞辛劳的居中联系;没有遍及各地各校的朋友们义不容辞的比对所有抄袭稿件;没有各校系办行政人员辗转协助通知受害者;没有所有发自内心的打抱不平、温言安慰和耐心商量——单凭我一个人,即使再愤怒,一定也早已学会乖乖闭嘴,从此沉默。
本人深知这个世界每天都发生著更值得大众关注的事,“几个无名的人文科系研究生被抄袭”可说是轻如鹅毛,此则冗长的声明若是造成困扰,敬请见谅。即使如此惴惴不安,本人仍执意联合所有受害者发此不平之鸣,除了希望资讯公开透明,替所有受害者争取到应得的善后处理;更希望能以己为例,提醒同为人文科系研究生的大家。
面对恶意的抄袭,我们固然是防不胜防,但我仍希望能尽一己绵力,让大家相信我们仍可以关心学术;而那些为研究耗神的成果,哪怕再不成熟,都值得获得一份最基本的尊重。感谢所有耐心阅读的读者,也感谢所有愿意使此则声明到达更远之地的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