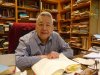编者按:本文选择孙康宜最新著作《奔赴》,联经出版。

早在普大当研究生时,我已经认识了余英时先生。当时余先生还在哈佛任教,他有一次被邀请到普林斯顿东亚系演讲(详细情况,请见本书第三章)。后来我又在一年一度的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的开会期间遇见他,所以早已是老朋友了。一九七七年,余先生从哈佛转到耶鲁教书,在耶鲁他一人跨两系,不但是历史系的讲座教授,也是东亚语文系的资深教授成员。所以一九八二年初,当我刚得到耶鲁的教书工作时,他和夫人陈淑平(Monica)都非常高兴,两人还打电话到普林斯顿向我们恭喜。不久,陈淑平还特别向我和钦次介绍纽黑文当地可靠的房地产经纪人,让我们很快就买到了满意的房子。
但我们一直到一九八二年九月初快要开学时,才首次见到陈淑平本人。那一天钦次和我到他们橘乡(Orange)的家中拜访,刚一进门,陈淑平就很热情地说,请我们以后就喊她做 Monica,喊余先生为“英时”,所以一时之间我们顿感轻松自在。以她的言谈和风度,Monica天生就是一个有教养的知识女性。她是陈雪屏先生的女儿,所以我迫不及待地告诉她,从前我在台湾念小学和中学时,曾获得不少奖状,其中有一张是我书法得冠军的奖状,那是她父亲盖章签名的,当时陈雪屏先生是教育厅长,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深受鼓励。听到这个故事,他们在座的两个女儿 Sylvia和Judy都高兴得眉开眼笑。而 Monica更是感动不已,说她下次打电话给她父亲时,一定会向他转告我的问候。(许多年后我才发现,原来就在我最初认识 Monica之前不久,英时先生为他的岳父八十岁生日献上两首诗,题为“贺雪屏丈八秩大庆律诗二首”,当时书法家张充和女士还特别为该祝贺诗用工楷写出,并加“福寿康乐无疆”等祝词,且加盖闲章“大吉祥”。陈雪屏先生一直把那幅宝贵的祝贺诗书法悬挂在他台北家中的书房。)
且说,英时最喜欢聊天,Monica又是个厨艺的拿手,所以自从我们搬去纽黑文之后,我们两家人经常相聚,很快也就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了。Monica和我尤其亲密无间,两人每星期都打电话互通消息。而且刚到耶鲁的时候,我正开始准备写我的第二本书《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所以我也经常向英时请教有关诗人陶潜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当时英时才刚发表了他所谓的中国思想“四个突破”的那篇文章,其中第二个“突破”正是汉魏之际,也就是陶潜之前不久的时代。此外,我也屡次向英时请教有关其他学术上的问题,也经常鼓励我的学生们到历史系去选修他的课。我的早期博士生苏源熙(Haun Saussy)就曾上过英时有关宋明理学的课,终生受益良深。
然而一九八七年的春天,英时却突然宣布,说他已在耶鲁教了十年书(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七年),但由于个人因素的考虑,他决定要接受普林斯顿大学的聘请,预备转去普大教书。对于这事,我和我的耶鲁同事们都有一种复杂的反应。我们相信,在游说英时的过程中,普林斯顿的校方人士一定是苦心积虑,曾经花过一番心力的,否则英时绝不会轻易作出这样的决定。后来我们才知道,英时早于一年前,在赴普林斯顿的途中,就已经写过一首诗,特意抒发他此次个人抉择之艰难。首先,该诗的首句标明了普大一事的偶然性:“招隐林园事偶然”。那就是说,英时从来没想过要“跳槽”,但偶然间来自普林斯顿的这个“招隐”的感召力实在太大了,终于赢得了他的心,使得他无法拒绝普大。所以诗中又说道:“榆城终负十年缘”,表明他不得不离开榆城(即纽黑文)的伤感。后来五月间,在英时与Monica离开耶鲁之前,我们还特别在家中为他们举办了一个欢送会,许多系里系外的师生都出席了那次盛会(包括傅汉思先生和他的夫人张充和女士)。就在那次聚会中,英时把他特别为我们重新抄写的那首“招隐”诗亲自送给了我和钦次。
当时英时给好友 Edwin McClelland的临别礼物就是他亲自抄录唐代诗人张继〈枫桥夜泊〉的一幅书法:“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张继这诗是日本人最喜欢的一首唐诗,所以Ed非常珍惜英时的这份礼物,还请当地最著名的画廊Merwin’s Art Shop把英时的书法加上美丽的镜框。后来二○○九年Ed去世后,耶鲁东亚语文系把英时的这幅字交给我个人收藏,至今仍挂在我的书房“潜学斋”里。
生命的曙光
那是一九七○年五月,普林斯顿校园正值春花盛开的时节。有一天钦次刚走进他的实验室,就接到南达科达州立大学(South Dakota State University)土木系系主任Emory Johnson的电话,说他们要聘请钦次为该系的助理教授,问他愿不愿意接受。在电话中,钦次立刻接受应聘,并说他的博士论文在暑期间即可完成,所以九月初就可以开始上课,绝对没问题。接着钦次立刻打电话给我。当时我正在ETS中心上班,听到这个好消息,很是开心,觉得那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道曙光。
在一般美国人的心目中,南达科达州是个蛮荒不毛之地(用今日的语言来说,是个“无依之地”),而且冬天全是冰天雪地,有谁愿意搬到那儿去住呢?但对钦次来说,才二十八岁就能得到一个美国州立大学的教书工作,可不容易。据说那一年全美国的水利工程方面只有两个教职的空缺——其中一个空缺是在美国大陆以外的波多黎各(Puerto Rico),另一个就在南达科达州。在如此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居然能获得一个教书工作,已经很幸运了。钦次的普大同学郭钦义也有幸获得波多黎各大学的那个教职。
八月间,我们匆匆离开普林斯顿,就开始了我们的西行之旅。我们顺着一连串的州际大道开去,经过宾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爱荷华等州,身上只带仅存的二十七美元现钞。中途除了几次下车吃饭、并在密歇根大学(Gram的儿子David Huntington家中)留宿一夜之外,我们两人只顾不停地开车向前行。一路上的风景十分特殊,因地而异,许多美好的景点都令人赞叹。奇妙的是,我们前后只用了两天的时间就开到了南达科达州的Brookings城,那就是南达科达州立大学的所在地。抵达目的地之后,我们方才发现,我们沿路已经习惯了这种浪迹天涯的生活,好像进入了一种崭新的精神层面。
我们一到Brookings城,就爱上了这个小城,从此我们就称它为“布城”。那儿的人特别有人情味。首先,土木工程系系主任夫人Joanne Johnson整天陪我们到处寻找住处,还主动安排我们在旅馆中的临时住宿,并让我们不必立刻付款,其热情和周到令人感动。而且,令人振奋的是,南达科达州立大学有个十分完备的大学图书馆。一听说我正在新泽西州的罗格斯大学攻读图书馆学硕士,那儿的馆长立刻决定要聘我为该图书馆的“资料图书馆员”(Reference Librarian)。但我得等到一年后,才能开始正式上任。
九月初,我只身飞到东岸,在短短的一学期之内,修完了所有剩下的必修课程,并于次年一月十五日返回到布城。但因为要等到七月一日才能开始到大学图书馆上班,所以我决定利用春季的期间先到南达科达州立大学英文系的硕士班选课。所以刚回到Brookings不久,我又开始过着学生的生活了。然而,当时南达科达州地区正陷入冰天雪地的困境中,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大开眼界,亲自见证了该地有名的暴风雪(blizzard)。有好几次,我们开车开到半途中,就被大风雪困住,只好把车辆弃置在路上,以爬行的方式慢慢回到公寓。那真是十分惊险的镜头,至今难忘。但也就在那种艰难的情况中,我们慢慢学会了如何在困境中求生存,如何培养坚忍不拔的潜力。
一九七一年六月初,我和钦次利用放假的期间,一起飞往东岸,主要为了参加各自的毕业典礼。(当时钦次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土木工程博士学位,我也同时得到Rutgers大学的图书馆硕士学位。)借着那次的旅行,我们在普林斯顿与Gram团聚了几天,很是愉快。记得Gram一直很关心我们在南达科达州的生活情况,所以她计划不久就要到布城来看我们。

孙康宜|奔赴:半个多世纪在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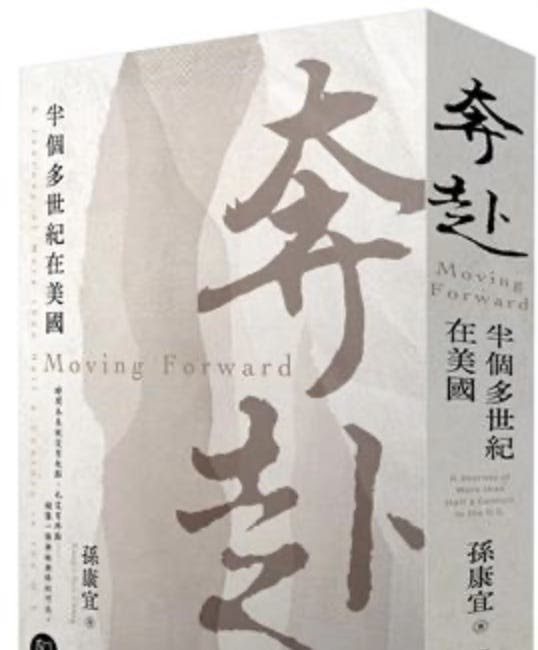
作者:孙康宜出版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日期:2024-06-13 ISBN/ISSN:97895708733821968年,24岁的孙康宜毅然赴美。曾目睹二二八事件现场、经历白色恐怖的她,从备受心灵创伤的失语症患者,到获选为学术殿堂的中研院院士,生命中充满了跌宕起伏的故事。纵然总有遭逢困厄的时候,孙康宜仍勇敢前行,“即使当前看不见将来的前景,但因为所到之处皆可取,让我们更加相信我们心中的愿望也还是可以企及的”。历经各种劫难与贵人,加上自我的积极振奋,终由深渊走向光明,自普林斯顿大学到耶鲁大学,化育春风,桃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