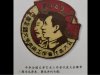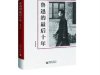很小的时候就读过鲁迅,记得小时候最早读的是一本连环画,讲的是鲁迅的故事。其中一个情节对小孩子来说印象非常深刻。这个情节是说,鲁迅在日本学医的时候,有一次看纪录片,内容是中国人被砍头,旁边有一大群中国人围观。连环画里的场面,至今我还有印象。鲁迅说他受不了国人的麻木和冷血,决定弃医从文,要唤醒国民,要在黑屋子里发出自己的声音。从此以后,中国人麻木、冷血,喜欢看杀人等等,在一个孩子的脑海中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又读到了《狂人日记》,其中一段话成为了经典: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在我年轻的时候,《狂人日记》看过很多遍,它给我的印象是,中国历史几千年来都是一个“吃人”的社会,中国人历来就残酷,从来就喜欢残忍,这个观念开始固定在我的记忆里。加上鲁迅的另外一篇小说《药》,主人公还拿烈士的鲜血蘸着馒头给儿子吃下去治病,这种印象更加得到强化。通过鲁迅的教诲,以及其他的一些言论的传播,例如对凌迟的渲染等,我当时真的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从治国根本的“仁义道德”到愚昧无知的普通百姓,从来都嗜血,从来都草菅人命,中国人的残忍似乎已成为彻底的定论。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道:“吃人的是我的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但是,那时候好像没想过,自己生于这样一个社会,是否也天生带着嗜血的基因?
与这种观念相对照的,一是西方对中国的落后、野蛮所做的批评,二是国人对西方热情洋溢的介绍。由此产生另一个关联的观念:西方社会是文明的代表,西方不管是制度还是老百姓的日常习惯都比中国先进多了。必须承认,有一段时间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对于中国以外的世界缺乏全面了解,中国的残忍是别人告诉我的,外面的文明也是别人告诉我的。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观念不太对。比方说,围观死亡的热情和嗜血的心理,并不是中国人的普遍现象。比较而言,欧洲人的这一爱好比中国人强烈得多。
古罗马的竞技场可以容纳9万观众,而这些观众最大的乐趣就是观看死亡,甚至还参与死亡的决定。古罗马竞技场里轮番上演的血腥场面,是整个民族嗜血心理的典型代表。后来我还知道,城市广场是欧洲文化的特征,中国古代城市没有大型广场,也没有大型群众集会的场所,欧洲古代展览死刑是在广场上,而中国古代一般是在城墙上。因此,中国古代执行死刑才会采取游街的方式,而不是群众集会。广场集会和游街相比,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
欧洲中世纪执行死刑和展览死刑,都有大量的群众围观,其人数远远超过中国。几万、几千群众围观死刑,在欧洲历史上屡见不鲜,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近代欧洲。而且,欧洲围观死刑的群众还很激动。就在鲁迅猛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吃人”之前不久,19世纪初,英国的一次绞刑有4000多群众观看。可能是广场不够大的缘故,也可能是没有罗马竞技场那种梯形观看台的缘故,也可能是一次杀人太少,群众难以轮流看到的缘故,4000名狂热的死亡看客竞相拥挤。一个犯人的绞刑仪式完成后,广场上又发现了100多具被踩死的群众尸体。我才知道,原来欧洲人对于他人死亡的热情远远超过中国人。
鲁迅《药》中的人血馒头只是小说的描写,具有特指的寓意。后来我发现,真实的群众“吃人”的狂欢场面,也多次在欧洲出现。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砍头后,很多民众涌上前去,用手帕、领带、衣服等容易吸收液体的物品,蘸取国王尸体上的鲜血,当场舔食。鲁迅说的人血馒头只是用来治“痨病”的特殊用途,而巴黎人舔食国王的鲜血,是想沾染贵族气息,比治病更具普遍性。幸亏死者是国王,否则他很可能就被群众当场吃掉。17世纪时,法国一个谋杀国王的刺客被公开以磔刑处死。这名刺客的身体被刑具撕裂后,民众冲上去争抢切割,有的就近烧烤,有的带回家,有的当场生吃。记载说,有一名妇女当场吃掉了死者的心脏。这次行刑后,有人写道,这名刺客是被巴黎“分享”了。我才知道,原来欧洲人比中国人更加残忍,更加嗜血。
我并不想否认鲁迅所说的中国传统有残忍的一面,但是,如果按照鲁迅的引导就简单得出结论说,中国人就是世界上最残忍的民族,我终于发现这个“既定”的观念是错的。中国人并不比西方人更残忍,更喜欢残忍,中国人绝不是世界上最残忍、最野蛮的民族。我认为鲁迅的这种做法造成了一个严重的误导,使得我在年轻的时候,上了他的一个当。但是,这不能责怪鲁迅,只能责怪那些用鲁迅的这个观念来教育孩子的人。我不明白,当初为何要拿这样残忍的内容来教育儿童?